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写在《吕梁日报》创刊50周年之际
□ 肖继盛
记不清哪位作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于这句话,我以为用于表达我与《吕梁日报》的情缘也非常贴切。
1987年11月下旬,方山县团委在方山一中与广大青年学生举行了一场对话活动。我作为学校团委副书记组织参与了活动的全过程,还写了一篇1300多字的现场新闻。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寄给了《吕梁报》。
没曾想到,到了12月底,校团委书记说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一进门,他却板着脸说,“继盛,看你办的好事!”正当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时,他忽然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报纸说,你看看。一拿起我首先看到了右下角我的名字,你若要问我当时的情境我真还说不出来,但你肯定会和我一样感到惊异,那么多的文字居然首先跳入眼睛的竟然会是自己的名字。可见,其实也许自己便是自己最亲密的恋人,只不过这次的红娘是我心心念念关注着的《吕梁报》。
这篇文章也是我的新闻处女作。
文章的发表,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之后便不时在《吕梁报》发表一个豆腐块或一张豆腐皮,并凭着这些豆腐块和豆腐皮于1999年4月调到方山县新闻办当了主任,且于当年办起了《方山报》,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报人。此后,渐渐地这当初的红娘——《吕梁报》就变成了我灵魂深处的朋友甚至是精神上的恋人,产生了无法割断的永远的情缘。
2002年5月8日,《吕梁日报》二版头条发表了我采写的《订单农业遭遇尴尬》的新闻调查,文章报道了方山县杨家会及其周边村庄在玉米育种中种子公司和农民共同存在的信用问题以及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科技意识淡薄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建议和思考。
自从调到新闻办,每次发现好的新闻素材,我都会给吕梁日报社的领导和记者朋友打电话讨教,他们总会热情地不厌其烦地给予指教。有时我还会请他们过来进行采访,有时他们也会冲着某个好的新闻或带着某些采访任务来到方山,于是在陪同采访的过程中便学到了不少东西。对于我发给报社的稿子他们都会认真编辑修改,而经过他们修改的稿子总是那样出彩,故而收获到了不少奖项。
在方山他们和我一块爬过山,涉过水,进过农家,入过厂矿。北川河畔留下了我们共同的足迹,山山峁峁有过我们匆忙的身影,在田野我们曾席地而坐与农民朋友进行交谈,在山野我们曾倚树而立聆听大自然的呼吸,在宿舍我们敞开心扉,海阔天空,直聊得月亮升起又落下,在野外我们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去捕捉每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山城巨变》《客从江阴来》《家里有了粮、山上有了树、兜里有了钱》《走进互联网的农民经纪人》《一个贫困县的教育结构调整》《他倒在了他赡养的孤寡老人家》……都凝聚着我与《吕梁日报》朋友们的共同心血,他同样凝结着我们永远的情意。而这种情意又使我在许多的时候,乐于把自己心中的情感向他们倾诉,于是便又有了一篇篇的小散文上了《吕梁日报》,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某些私下的倾诉。
2004年,国家进行报刊整顿,由我负责编印的《方山报道》被列在清除之列,相关部门不仅收回了准印证,注销了“户口”,还派人专门进行巡查。同时也有不少文章痛斥报刊泛滥的危害,有一篇文章尤其指出现在许多山沟里也办起了报刊杂志,很担心由此而妨害了写作的整体水平,妨碍了文学创作和新闻报道的繁荣,《方山报道》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当时作为总编辑的我觉得很委屈,很不公,同时也很无奈。种种指责总让我感觉到天天吃肉的人,想剥夺了吃不起肉而吃土豆的人的吃土豆的权利,甚至于有对吃土豆吃的那么香甜的眼红。我委屈还因为我们办这么一张小报,一不发表反动言论,二不妨碍社会稳定,三不瞎闹铺张浪费,四不低俗败坏风气。只不过想借此平台宣传国家大政方针,县委、政府工作思路,纪录社会发展,讴歌时代精神,同时也为当地新闻和文学写作爱好者提供一个得以展示自己风采的平台,让那些吃不起肉的人能吃上香甜的土豆而已。
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我将我心中的苦闷与不解倾诉给了吕梁日报社的朋友,他们在给予我安慰的同时,帮我和相关人员进行了通融,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报纸终于得以保留,只不过换了个名称。
2006年年末,我离开了新闻办到其他单位任职,之后又兼任了方山县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期间《吕梁日报》同样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凡写我单位开展的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的新闻报道只要发下去,总会见报。我知道这是报社同仁以另一种方式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同时报社的朋友们来了方山也会不时地联系我,让我深深感受到我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2016年7月,我退居二线,今年一月退休。但退居二线后,我并没有闲下来。《方山县志》《走近方山乡村》《方山县革命老区发展史》《方山党史》,我都是重要的编写者之一。同时亦有不少单位请我做写作、廉政文化、传统文化、党史等讲座,许多比赛活动请我当评委,生活充实而富有意义。
于是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一场对话活动,我就不会写出那一篇新闻。如果写了,没有被《吕梁日报》选用,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文章,当然也不会去了新闻办。没有吕梁日报社各位领导和记者朋友的关怀和关爱,我的写作水平就不会有大的提高。离开工作岗位后或许就只能去打打牌,下下棋,唱唱歌,唠唠嗑,或混在大妈大爷堆里跳跳那广场舞,用于打发那余下的岁月。这样,书中就不会留下我的名,讲堂上就没了我的声,这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不爽啊。
于是我庆幸命运给了我这么好的安排,使我与《吕梁日报》结下如此深厚的情缘,同时并默默地想,若有来生我愿与你再续前缘。
(作者系原方山县新闻办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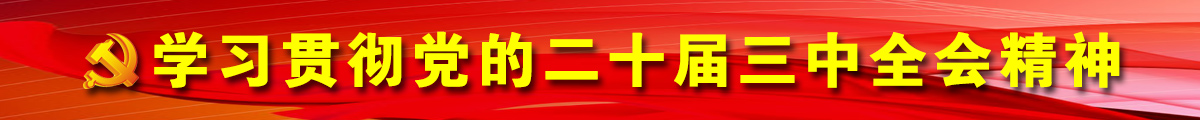

525bc6cb-fc0b-4b8e-8046-002bb3b8b48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