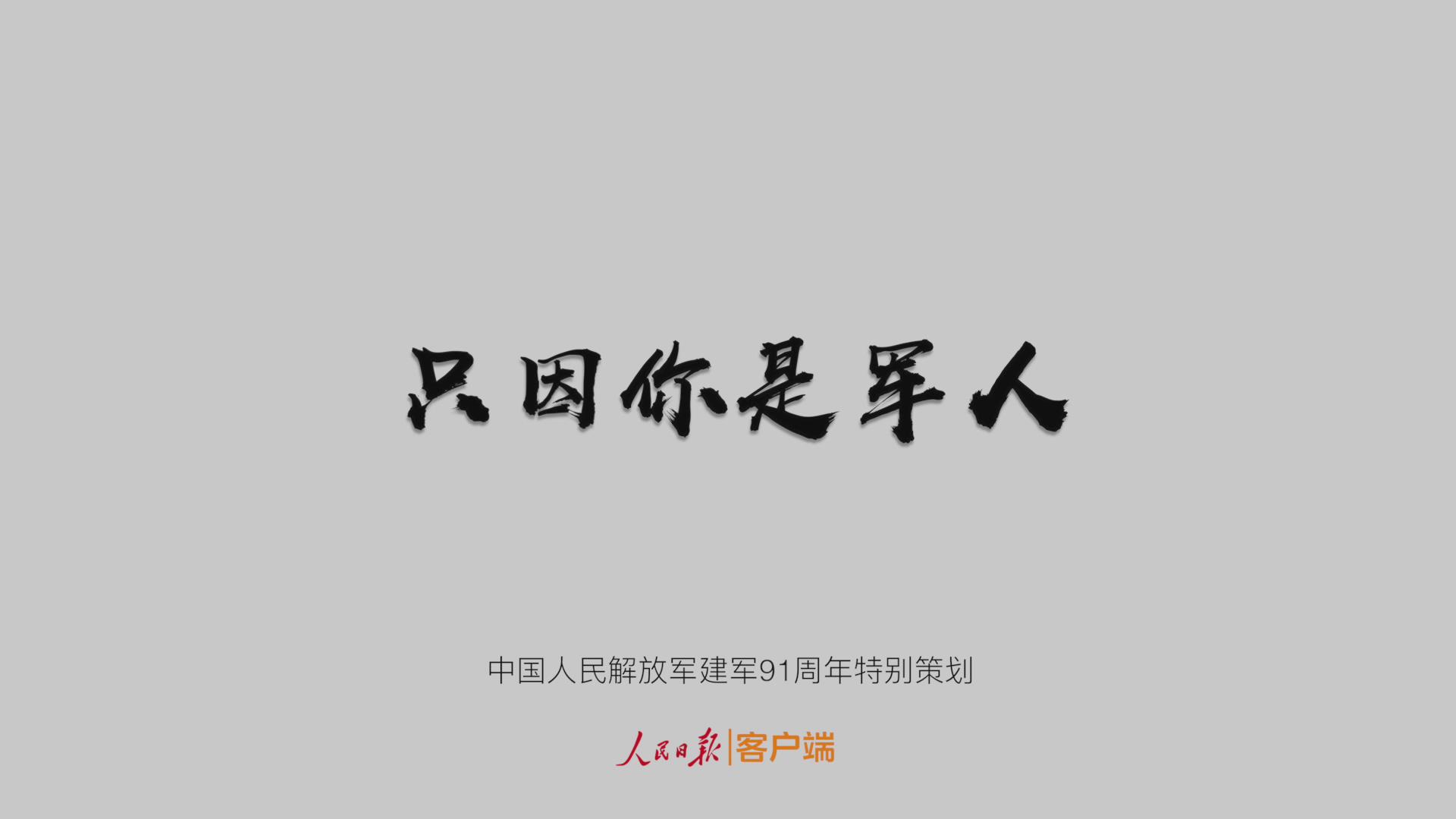苍儿会感怀
□ 李够梅

此行,本来就是来玩儿:看看青山绿水,贪婪地呼吸新鲜空气,如此而已。直到最后……
一
最后,踏着一串隐没于草丛中的古老石阶曲曲折折地来到一方平台。这里,没有建筑,但有几断残垣,有几通石碑,有一面好健壮地九十度角直立的石壁。残垣断壁上隐隐的壁画,仔细端详可依稀可见牛头马面和穿着官服的人;石碑有顺治年间的康熙年间的……据说那通立在乱石乱草丛中的当是最古老的,上面记载着东岩寺的建筑年代要比洛阳白马寺还早一年,看看无处下脚的样子,我没有走到跟前去看,只投它以尊崇的目光——它这样的年纪,值得我尊崇呀。
而石壁,上面分布着一个个方形洞口,洞口中探出一棵棵碧树。他们说,这些洞是过去和尚们的闭关洞。
我忽然就感觉到了一种关乎生命的强大感染力。
我似乎觉得这些洞穴都散发着人类对生命的庄严的探究;那些长在石洞的树是不是闭关修行的人永恒的精神化身?
于是,这周围的一切:壁画、石碑、石阶,甚至于大山的一草一木,都好像有一种从亘古一直活到今天的淡定从容。假如它们愿意开口,任谁都可以讲述一本般若经。
古人在画这些壁画的时候,只是要表达自己心中的信仰吗?抑或,也有他们的疑惑。他们是存心要向后世讲述些什么的,他们要跨越时空与后人交流。
交流一直都在进行,直到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同样接收到了千百年前先人的信息。面对这样的交流,谁能说这古寺遗址是没有生命的吗?
还有这石阶。年代使它们已不怎么平整了,但足以成为一条货真价实的路。
下山的时候,我设想:所谓生命,不仅仅是眼前能够看到的花、草、树木以及同行的人。古老的石阶、斑驳的壁画、闭关洞里伸出来的枝梢,无不透着灵魂的信息。不同时代的碑刻给阅读的后人这样那样的提示,然而那些灵魂本身静默不语。也许,某一天会在这寂静的山路上走来一个人,他无需苦苦参读,自然地就会和远古之灵融合如一?
关于东岩寺的一点感觉,仿佛一粒泡滕片,在我心里渐渐融化,进而和这次在苍儿会所见的一切融合。到处都充盈着生命的感动!
二
记得那个晚上,仿佛一种礼节性的座谈会开完已经十点多了。我第一个匆匆奔下楼去,却没有回房间,而是直奔楼外。一个完整的漆黑!
整个苍儿会,淹没在黑暗中,安静到了极至!我直扑门外,为的就是来约会这份黑暗与安静!小时候在农村,这样的夜晚是常态:“伸手不见五指”是那时作文里用于形容夜晚的常用语。
黑暗中抬头,就看到了预见的星空。自从那年在青海湖畔黑马河镇不期而遇了一幅美丽的星空,我就长久地思念着它了。今晚,在这样一条山沟里的这样一个夜晚,当有此景!天空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我想就在这样的黑暗中找个地方坐下来静望星空,那样,我想我会与几十年前的自己神交起来,我会安慰那时候心底茫然的自己,而那时的自己也会抚摸如今已经不再年轻的自己吧?
然而,短暂的几分钟后,其他的人一个一个陆续走出来了,王总善解人意地打开了楼门外的灯,照亮了近前的一方天地。热闹霎时打破了夜空。
我已乏了,还是回去睡觉:苍儿会,明早见。
早晨的苍儿会真像一颗苍翠的明珠。
我走在它的小径,侧耳倾听清脆的鸟叫声。一只黑白相间的小鸟在前面的石头上落下来:好俏丽的精灵呀!我端起相机对准了它,它却机伶地在我按下快门前飞走了。如是者再三。当我以为是自己追着看鸟的时候,鸟儿却戏耍了我。也是,我这样一个在城市生活中迟钝了的人,怎么可能和这大自然中的精灵比敏锐?
我只好老实让它自己好好呆着。我贪婪地去看远山、近树、湖泊、小草。深浅不一的绿。朱自清有一篇题为“绿”的散文,是专门写给仙岩的梅雨潭的。他写:这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能明眸善睐了……我想,我眼前的这无边绿色,绝不逊于朱自清的梅雨潭!
走走,看看,听听。然后我脱去鞋子,走进草坪。
挂着露珠儿的草坪松松软软的,很舒服。我舒展开自己,左推右送,打一趟太极拳套路。这么美的环境,正是修身养性的极佳场所。
三
寻找神树。
树之为神,通常并不是树的本意,而是人奉之为神。这是人对一棵树表达敬意的方式
这棵神树,是一棵公式树。公式,谐音才、材,寓意已然非常吉祥,难得的是,树干粗壮需四人才能合抱,以这种树的生长速度推算,树龄当在千年。千年的生命,经历了多少风霜雪雨,经历了多少世事沧桑,而它依然枝繁叶茂,可见是有修行的生命。在我们的文化中,尊崇历经磨难而更见坚定的精神。
见到神树之前,一行人跋涉于崎岖的林中小径。大大小小的树木走过无数,可以说每一株树都以不同的生命姿态站立着。有的端庄,有的妩媚,有的葡公式,有的扭曲,有的杈丫剑指,有的盘根错节……它们本是树木,但我一路看来,不由想到的却是在各处佛教大雄宝殿里看到过的十八罗汉。是呀,树木如果化身为人,这一个个形态各异而又纯粹天然的样子,可不就是如探索生命真相的罗汉们一样?
每一个生命都是天真的。因而都是可爱的。
就算几枚新鲜的松塔,虽然是常见之物,因处于这所有的生命都峥嵘着的环境中,似乎更加矫健。
有健壮的,自然也会有萎顿着的,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有那么一棵枯萎了的树木,悬空横卧着。它的身躯布满枝丫,说明它也是葳蕤过的。那么一棵壮年的树却死了,仿佛一个壮年的人突然遭遇了天灾人祸,总是让人心里会有深深的惋惜。
走了又走。走在最前面的人大约走成了惯性——只管走下去。然而,这次活动的导游,苍儿会山庄的王总却喊了:“回来,超过了。”
千年公式树就在隔着一条壕沟的路对面了。树身果然壮实如塔。
树身缠着许多的红布。在许多名胜古迹都见过这种:一棵树古老到一定程度,被奉为神明,拜山拜庙的人们在它面前许愿并结以红带,期望得到保佑。只是,这里原本荒无人烟的样子,古树竟也同样承载着世人许多世俗的期冀?
其实,同样是生命,而且人往往很狂傲地自诩为高级生命,却为什么让另一个生命额外地承载其他许多生命的愿望?大树无言,默默俯视脚下虔诚的人们,它大约很奇怪这伙移动的生命:他们为什么不像自己一样,把根深深扎入地下,使劲儿吸收生命养分?
四
前去探路的王总,意外地发现不远处有古村落遗址。大家猎奇的心理顿时高涨。
其实谈不上古村落,只有几截儿断壁残垣、一片石磨盘半截埋在土里头。看起来,不知道什么年代,这里曾经有一户人家居住。别人忙着在这里留影拍摄的时候,我往远处走了走,并没有看到别的房屋残迹。树木远远近近地延伸分布,使这个地方显得幽深美丽。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形成这种独户村?又是什么原因使这独户不复延续存在?我们这拔人里尽是些作家,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以此为背景创作出一部或曲折离奇或悲怆伤感或荡气回肠的小说来?想必会很耐读。
这个石柱,是曾经的拴马桩吗?到处是大树,何处不能拴马?若非人家讲究,则当是别有用途吧。
好吧,我也在这里留影以作纪念。我喜欢这沧桑的感觉,好像有很多故事的样子。我还用自己手里的相机很认真地去拍一株残墙缝隙里长出来的野花。花儿虽小,但容颜娇俏,与破墙形成极明显的对比。不远处有人朝我喊:你那是要考古吗?那么注重细节。他哪里知道,我考的恰恰是新,是一株非常不起眼的小野花。我从来就是一个抓不住或者也不想抓重点的人。
五
前面提到的那个所谓古村落是意外撞到的。事实上,我们的计划里,看过神树,的确有两个村庄遗址要看。
穿着厚底凉鞋走这种崎岖山路,我的腿脚可是有些受罪。年纪大的或体太胖的,在寻找神树之前就歇脚了。所以再要走时我略有犹豫。但还是不舍,这样原生态的山梁沟峁,并不是经常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
一堵土墙与两棵大树相倚出一份古老的安宁;一座废弃的院子柴扉完整诉说着曾经的温馨……然而不是这里,再走。
一路上并没有见有人居住的村庄,却见过一群又一群牧养的牛。牛们神态安详,吃草或者卧地休息,牛犊倚在妈妈身边。
第一个村庄,我以为叫废弃的村庄比叫古村落实在些,古村落,需要有历史的支撑:一处处屋舍?落分布。人去屋空,有的做了牛圈,想来是近年来迁居出去了,毕竟在这深山密林的地方生活,要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方式和节奏接轨,有太多的局限。
我爬上一个土坎,那里有一块相对大的平整地面。从一个歪卧着的石碾槽猜想,这里可能是村里的打谷场之类的地方。我在槽上坐下来休息片刻,闭上眼睛感受山风习习和阳光的照射,忽然想起“接地气”这个词。现代人讲究养生,有些养生专家就呼吁人们要注意接地气。然而人们却又苦恼于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找不到接地气的地方。这山林中是绝对接地气的地方,却又被人遗弃到遥远的身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果然是一对矛盾。
人类社会有许多矛盾存在,消弥矛盾才能让我们更加和谐幸福地生存于天地之间吧。
第二个村庄,的确有些古村落的味道了:一座斑驳的老桥,一个稳重的拱门,几块散落的石碑,都已经是历史在说话了。因了这些因素,这个地方更显意味深长。
既有古,当可怀古。只是碑刻都有些模糊,人又走得疲惫了,我己无心去辩别那些历史的痕迹。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且欣赏依旧的青山,历史交给有文化的人们去考量!铁戟沉沙,总会有人史海钩沉。不论钩得出与否,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生总是短暂,历史总是厚重。只有那些用足够的经历厚重了自己人生的人,才能走进更加厚重的历史中去。
我这样一个追求轻松的小女子,不想那么多,且去看天看云看草看树,如果能看出些许门道,作成一朵不起眼的山里小花,何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