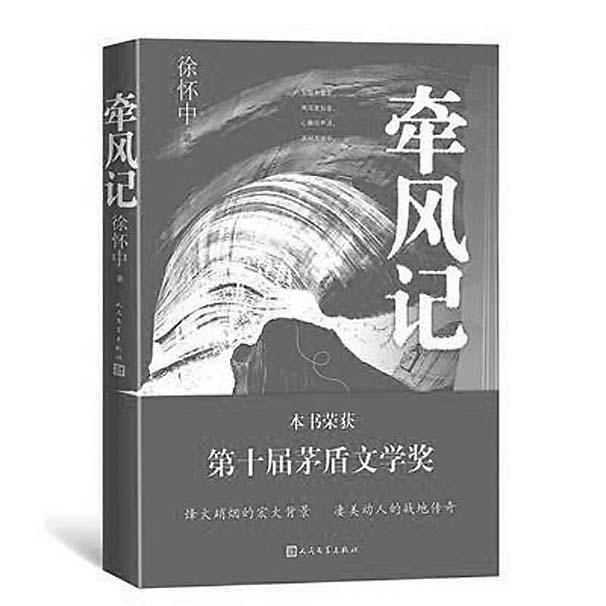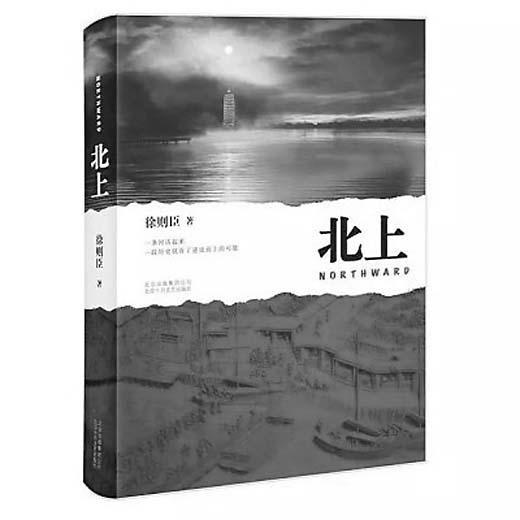一切文学史都是流动的,犹如历史的长河一样在流动。文学艺术是发展变化的,它在随着社会和时代发展而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尤其当下,面对中国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城市化、现代化、一体化、全球化、科技化,都使得当下社会产生了加速的变化。社会加速,使得人类在空间、物、行动、时间、自我五个方面产生了大规模的变化,甚至异化。自然,对此进行反映和表现的文学艺术也要发生变化。
《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中说:“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国精神。对于深刻反映时代变革、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
8月16日,为公众所瞩目的第十届文学奖在北京揭晓,五部获奖作品,依照得票多少的顺序,分别是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那么,我们从这些获奖的优秀长篇小说中,究竟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在当下的哪些格局变化与发展趋势呢?
一、乡村文学的锐减及其结构性变化
这次获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乡村文学,也就是没有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在过去的历史中,乡村中国一直是文学最重要的叙述对象。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产生的现代文学,本身就是乡土文学的建立,鲁迅、沈从文等都是典型的代表作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翻身做主,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题材的文学成为最突出、最主流的文学,直至改革开放,都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脉,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家,譬如山西的“山药蛋派”作家。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或乡村文学转移,其实就是现代性在中国的被动性和植入性所致。对现代化的追求,使得城市与乡村的对照由此衍生,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自然也形成各自的对比。自然,乡村向城市的进发就成了一种本能的主动。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就是典型的代表。因为“城市成了农民向往的地方,因为那儿有不尽的财富和诱人的享受和快乐。同时还是个使人有出息的地方,农村的优秀人才都到了那里,那里有学问,更有权势。就某种意义而言,农村的正式领袖已经部分地流入了城市,化为新市民。”(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乡村一直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动同化,自然,乡村文学也在不由自主的式微、落寞和消减。尤其在当下,50后、60后的作家虽然还在中流砥柱,但70后、80后、90后的作家正在脱颖而出,成为主体,他们是基本上没有乡土文化记忆和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这也是乡村文学锐减的真正的主要原因。
就是在50后、60后作家的乡村文学作品中,也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这就是整体性的瓦解和破裂。贾平凹和阿来等作家的表现乡村中国的长篇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叙事整体性的碎裂。贾平凹以往的作品都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都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推动故事或情节的发展。但是,他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已经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令人震惊的情节,也没有所谓形象极端个性化的人物。清风街上只有琐屑无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复一日的庸常日子。“秦腔”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小说的叙述者是疯子引生,引生痴情地爱着白雪,不仅是因为白雪漂亮,重要的因为白雪会唱秦腔,这有一些对某种文化或某种文化传承的一往情深。白雪、秦腔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乡村中国最后的神话即将成为过去,清风街再不是过去的清风街了,世风已经改变了一切。阿来的《空山》,也是几乎没有值得讲述的故事,拼接和连缀起的生活碎片充斥全篇,在结构上也是由两个不连贯的篇章组成。《空山》第一卷讲述的是私生子格拉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他们屈辱而没有尊严,甚至冤屈地死亡,人们对此浑然不觉。卷二《天火》中,那场没有尽期的大火不仅照亮了自身,同时也照亮了卷三《随风飘散》中格拉冤屈的灵魂。格拉的悲剧是在日常生活中酿成的,格拉和他母亲的尊严是被机村普通人给剥夺的,无论成人还是孩子,他们随意欺辱这仅仅是活着的母子。原始的愚昧在机村弥漫四方,对人性的追问成了《随风飘散》挥之不去的主题。它与《尘埃落定》宏大的历史叙述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对比。
二、城市文学正在强劲崛起
城市是乡村的对应物。那些思想家、哲学家们说的好:乡村是上帝创造的,它是自然的;而城市人类创造的,它是人根据自己的欲望创造的天堂。斯宾格勒的在《西方的没落》说:“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城市由于逐渐地脱离了乡村并最后使得乡村破产,成为高级历史的进程与意义所一般地依从的决定性的形式,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是的,“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这是乡村必须面对的命运。但是,城市也绝对不是抒情的世界。批评家张柠说:“它是散文的世界,是黑格尔所说的散文的世界,是席勒所说的‘感伤的’时代这个就是现代文化,城市文化,它瞬息万变,飞速发展,高速移动,对此,我们是没有办法抒情的,它只能叙事。抒情和叹息到哪里去了?它还存在吗?可能还有,还在那里,但不确定,充满疑问,无以言表。那种情绪和心绪是在那里面,是通过词语的缝隙散发出来的或者挤出来的,你要捕捉,要寻找,要拼贴,所以才有文学批评这个专业”。古代是没有这个专业的,有的只是文学鉴赏。
这次获奖的五部小说中,除《牵风记》为军事文学外,剩下的四部都可以称得上是城市文学了。《人世间》当然是城市文学,它皇皇三大卷,115万字,以周氏三兄妹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写出了城市平民近50年来生活的巨大变迁。不过,它写的不是像80后作家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写的是国际大都市上海最有钱的人的富豪生活。《人世间》主要写的是“东北-城市-平民-工人”的生活故事,它是一部近半个世纪中国城市平民的生活史,是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史,是底层青年不懈奋斗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书写“好人文化”的向善史。《应物兄》是写大学生活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应该也是城市文学。它主要以济州大学筹建儒学院,联系儒学大师程济世归国及其与相关人物周旋的应物兄为叙述中心,将他与各种人物的打算、想法以及冲突、矛盾汇集于儒学复兴,由此带出知识人的历史和现实、名誉和利益、欲望和心理等复杂关联,既信誓旦旦,众声喧哗,又一地鸡毛、鸡零狗碎。有意义的悲喜剧与无意义的荒诞反讽都相互纠缠。这也只有是城市里才有的生活。《北上》虽然是以1901年和2014年两条时间线去写大运河这条河流的变迁和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但它主要还是写的是大运河两岸的城市平民生活,也可以勉强称的上是城市文学。《主角》是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人生际遇为切口展开书写的,但它很好地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革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社会的大发展和时代的大变革,书写了中国城乡近半个世纪改革开放的历史沉浮与巨变。
三,现实主义文学书写正入佳境和大放光彩
现实主义写作一直是茅盾文学奖所鼓励和褒奖的一种主流文学。其实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基础就是人民性。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刚到,很快就遭遇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对人类的理性逐渐产生了严重怀疑。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代表,通过对人的无意识的“揭发”,那个充满自信的理性世界逐渐崩塌。伴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体意识而产生的现代主义越演越烈,很快形成主流。但对社会解放和发展的关怀,对无数的广大普通劳苦大众的关怀,依然使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和生命活力。再者,现实主义对于“真实”的追求,蕴含着人可以通过观察自然、理解自然而获得某种类似于上帝的“真理”有关,也内含着欧洲哲学源头柏拉图思想中所想象的作为一种完美“理念”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生生不息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这次获奖的五部作品,大大彰显了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强大生命力,充分显示出了“无边现实主义”的雄风和力量。《人世间》和《主角》都是非常庄重的、严肃的、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人世间》属于比较典范的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书写分式,从知青插队、三线建设、工农兵大学生到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国企改革,再从“下海”、职工下岗、棚户区改造到现在,是对外部现实的逼真模仿,塑造真实可感的社会氛围,一系列层次分明、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认知价值,写出了从是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血肉丰满的人,写出了形象的、具体的、可触摸的、艺术的人民性,写出了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蓬勃向上的基本力量。《主角》最大的价值,就是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美学魅力。忆秦娥的成长道路和性格生成反映出了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印记,时代的变革又成为人物性格生成的动因,在空间上尽可能地写出了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卷,重申了人物形象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牵风记》以其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给现实主义注入了活力,通过“三个人和一匹马”,写出了战争中的人性、爱情与美,为战争题材的写作走出了一条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理想主义写作道路,塑造出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少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汪可逾和齐竞。《北上》和《应物兄》都是带有现代意识的现实主义书写,前者涉及历史、地理、考古、摄影、绘画等许多知识和细节,具有现代主义小说“综合性”的重要特征;后者更是以一个刚刚发生车祸死后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应物的瞬间,作为叙事的起点,写成的八十五万字的一次记忆返还,以第三人称视角来叙述,叙述者称主人公为“他”或“应物兄”,或者“我们的应物兄”,大大拉近了叙事者、读者与主人公应物三者之间的距离,皮笑肉不笑,充满了反讽和自嘲。叙述者直接或间接转述的那些言说,以及镶嵌在故事情节中的对话、讲学、论道之语,让人感觉到小说中不止一个叙述者,也不只有一个声音。所以说,是一部现代意识与中国经验紧密结合的知识分子之书。
四、世界视野的确立,使得当代中国文学正在接近歌德“世界文学”的概念
70后作家徐则臣的《北上》获奖,无疑也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一大亮点。一则这是70后作家在茅盾文学奖“史上”的首次获奖。二则《北上》这部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有两大特点:一是叙述时间的使用,作家选择了双线并行,上下交汇。一条是1901年,从时间的上游顺流而下,意大利青年小波罗来到中国,顺着大运河北上寻找他的兄弟马福德;一条是2014年的溯游而上,通晓外语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谢平遥正在寻找祖辈们的遗迹遗物,拍摄大运河纪录片,去“世界”寻找改变中国的药方。历史与当下交汇,东方与西方文汇,都糸于这一条大运河之上,时间成为这部小说的重要枢纽;二是世界视野的引入。“徐则臣以一种比较的视角介入《北上》的写作”。70后评论家张莉说:“小说家对‘世界’的理解不是单边的,不是狭隘的。……欧美对于谢平遥来说意味着‘世界’,中国对于小波罗而言也意味着‘世界’。这是小说家的卓越理解力,小说不仅要写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运河,也写‘他们’,即西方人如何理解我们的运河。相信诸多读者对小波罗离世的场景记忆深刻。他的遗言是,‘京杭大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这是一个细节,但它具有隐喻色彩。《北上》里,固然有作为中国人的强大主体性,同时也有一种并不封闭的世界视野,换言之,世界视野使徐则臣写出了运河的中国气象,也写出了运河文明的世界意义。”(《文艺报》2019年8月23日第3版)
早在1827年,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话录》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这是一种世界五大洲的“总体文学”的概念,正如美国的评论家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中所说:“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一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而每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但是,他们又说:“但是,歌德自己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理想,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放弃其个性。”但我觉得,《北上》这种世界视野的确立,使得当代中国文学正在接近歌德“世界文学”的概念,正在开始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与世界范围内书写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我觉得,这是一种要把个体放在世界与时代大平台上生发意义的文学写作,是一种对个人生活世界与价值意义世界进行“契合”性思考的文学写作,是一种从眼前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历史逻辑与未来走向的文学写作。是应该受到鼓励、肯定和褒奖的文学写作。
五、70后、80后作家正在成为当代文学的创作骨干
《北上》的获奖,距离四年前《耶路撒冷》的提名,已经显示出了茅盾文学奖对于年轻写作者的年龄松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约翰·契弗说:“唯有文学能持续地清晰地记录我们力争卓越的过程。”文学是一种前赴后继的写作事业。获奖的《北上》(徐则臣),以及提名的《北鸢》(葛亮)、入围的《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石一枫)、《陌上》(付秀莹)、《慈悲》(路内)《悬浮天体》(田耳)等等,都已充分显示出了70后作家的创作实力,一批80后作家也紧跟其后,步其后尘。他们已经走出了没有力量、没有承担、没有关怀的所谓“文学精品”的写作,他们作品已经具有了历史感,开始了对于人的精神疑难的深度书写,开始了对于历史隐秘与深暗处的探索,开始了对于比他们的时代更久长的现实书写,开始了向着辽阔星空的奋力跃起,他们正在以充满个性和魅力的创作,开始了对于时代和历史有所思考的写作。正如70后评论家张莉所说:他们开始“关注人内心的深度、人的希望与疼痛,爱和恐惧;他们的书写的是我们耿耿难眠无以言说的那部分;他们在尽可能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生而为人的意义,写下我们生而为人的尊严所在。”
不可否认,70后、80后作家,以及90后作家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骨干与主体力量,但是,同时也不可否认,他们的文学作品欠缺一种对历史与时代的“总体性”力量。他们还缺乏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与时代巨大变革的整体建构性“赋形”能力,缺乏对当下的现实生活用总体性眼光进行整体性关切和打量的思考。如何透过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探寻时代发展的动因与趋势;如何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与全球范围内书写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如何有力地书写出了当代中国的眼前现实,生动活泼地塑造出当代中国人的形象,对于他们而言,还真的是一种很漫长、很艰辛的文学书写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