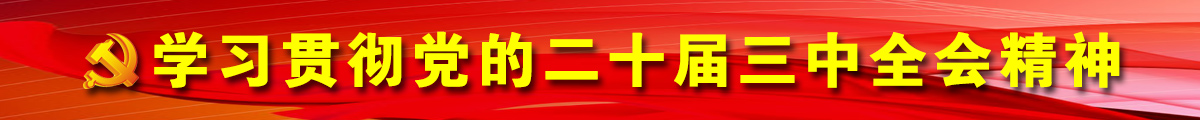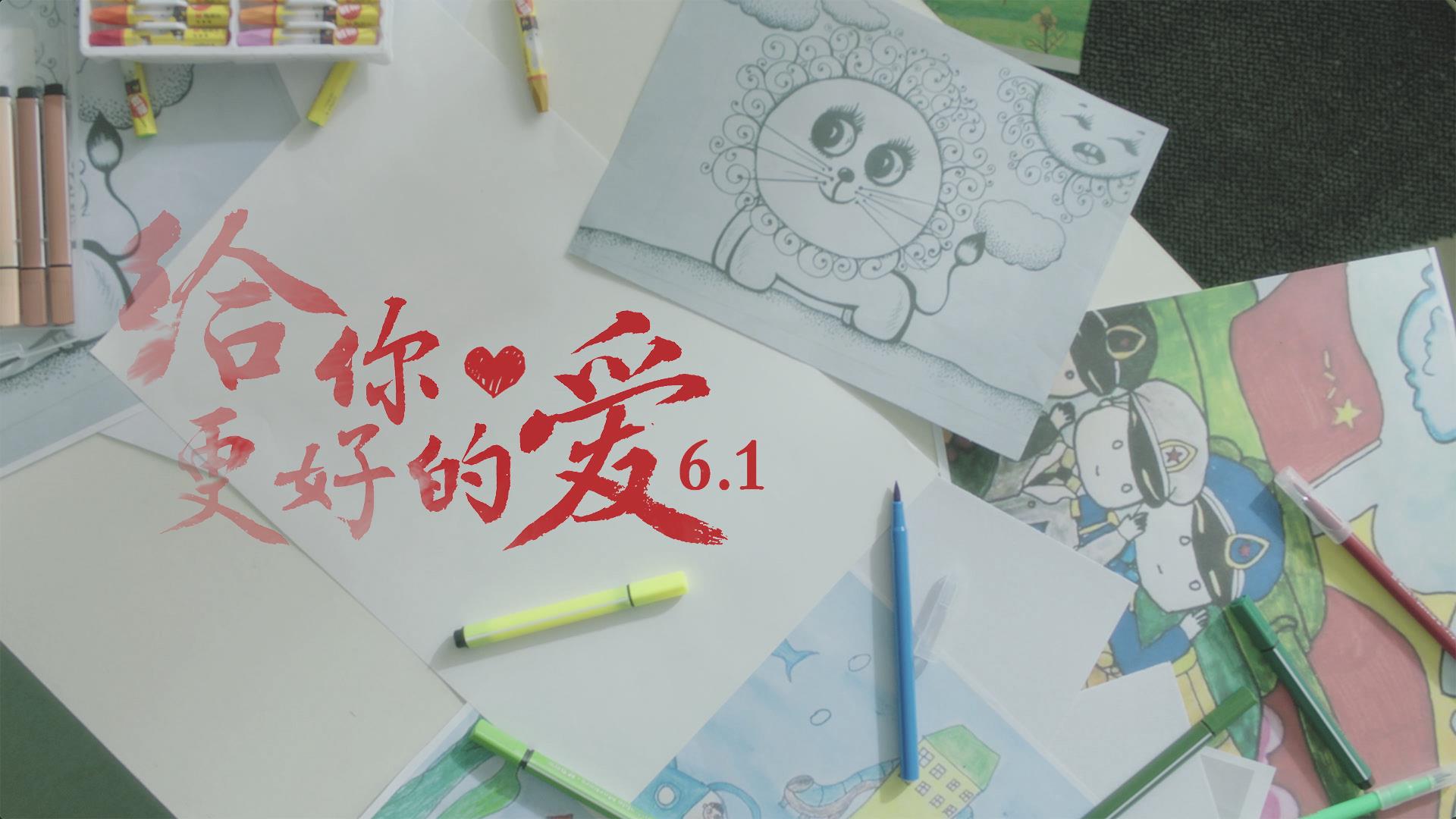一抹淡淡的清芳
——评马鸿宾长篇小说《丁香花开时》
□ 张子影
翻开赫赫然数四十余万言的厚重之作,宛如翻开大自然的书页、大社会和大历史的篇章。鬼使神差,天随人愿,这里发生的重大事情总是在丁香花开时。
《丁香花开时》如一幅徐徐铺展开来的画卷,在空间的延展中,把地处黄土高原内陆柠州的乡村世界,从泥土般的灰暗沉闷渐变至色彩的斑斓生气,每一处线条都细细加以描摹。一个文化世家,近百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着百年的爱情故事。
作家格林说过,一个人在二十岁以前,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形成了,此后一生的写作无非是在咀嚼青春所留下的记忆。边城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香椿树街之于苏童,都有地理学和精神学的符号意义。马鸿宾以地域为结构坐标和参照,先后写出《风生水起》《丁香花开时》两部不同的长篇小说。柠州是他自己划出的一块文学土地。如果用世家图谱来表示,那么这个地界里栽了很多树,每一棵都是独立的,枝繁叶茂,这些树的根脉在地下联结着,长出地表的却不是同一个主干。可以看出,这部书马鸿宾是在试图还原民国以来柠州的物质世界,一种俗世生活。书中写到峪道河、桑沟、水泉、南开社、铭义中学、河汾中学、四川金堂、成都瑞士领事馆等都是真实地名,城内以鼓楼底十字街心为中心,沿东、南、西、北主干大街各类店铺鳞次栉比。在美国传教士万德生的眼里,当时柠州城“文明不次平津”。从这个意义上说,《丁香花开时》的文学是市井的、乡村的、也是人世的,他在用有限的柠州社会涵盖无限的世界风景。
这部书总体上是有原型的,作家结合府志地方文献,深入野畴和民间专访,力图将柠州区域社会这面至今已破近百年的镜子进行重组,以求折射出当时的生活,反观今日的社会百态。小说的骨干部分、一些故事和人物就是这样形成的。作家写出很多东西,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必、也不可能亲身经历的,这就要借助于作家的想象力来完成。想象的幅度越大,越是需要依赖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经验,才能够把这大幅度的跳跃、这之间形成的巨大鸿沟填平。作家出生在山西柠州城东的一个乡村,他本身就是一个“城乡结合部”,谈农村通达谙练,论城市烂若披掌。在他心里装下许许多多城乡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故事。
书中多以城市题材展开,同时一个峪道河的乡村版图若隐若现。峪道河娘娘庙村是马鸿宾的姥姥家,他从小跟着母亲在姥姥家居住生活;这里曾是柠州医院的疗养院、铭义中学的夏令营部,冯玉祥、高桂枝、费正清、梁思成、林徽因、史迪威等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故事耳熟能详,峪道河水让他的心情时而激越时而黯然,难以平静。这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穿越整个世纪,从民族的命运到个人的命运,无法视而不见,所激起的每一道波浪,所泛起的层层涟漪中,似乎都有太多的故事需要诉说。
本书的结构就像是一座书中所写的基督教教堂,有塔楼,有穹顶,有巨大的石柱,有豪华的大理石地板,有镌刻,有精美的彩绘。它不是通俗文学按时间顺序的故事讲述,属于现代纯文学的一种诗性写作。总体上,以柠州铭义中学、柠州医院和高护校为原型的大的故事是同时呈现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当读者顺着它的情节往前走的时候,另一个故事板块就自然地穿插进来。但走不了太远,这个故事好像是在呼应已过的情节,有时候虽然也会荡开一点,但不同的线索很快就会合二为一。有小溪般的热闹,也有大海般的平静;有壶口瀑布般激流勇进的河段,也有一马平川舒缓的地方。有的情节看似稍有游离,像思绪片段、哲学笔记之类,它正是对深邃曲折的人性进行深入的表达,有思想的幽深: “深邃的天空容忍了雷电风暴一时的肆虐,才会有风和日丽;辽阔的大海容纳了惊涛骇浪的一时猖獗,水才有浩淼无垠;苍莽的森林忍耐了弱肉强食一时的规律,才有郁郁葱葱,泰山不辞寸土,方成其高;江河不择其流,方成其火。”这些都与通俗小说不同,因为更酣畅淋漓,也更为服从于心灵的要求。这部书写得那么随意、和谐而又极其巧妙地把宗教、文学、人学、思想、哲学、音乐融合在一起,让读者眼花缭乱。
小说不乏悬念和冲突,情节被感觉所浸透,动作和内心相连,成为一场生命富有想象力的演出。本书在序曲部分、大的章节的转换都有伏笔,特别是余前昭和傲雪在蜀道上的日日夜夜里,情节跌宕起伏,多少次险象环生。
人物是小说着力塑造的形象。在小说的多种元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还是人物。作家赋予了主人翁余前昭生命,他折射着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恒慕义、余心清等的影子,作家对他特别欣赏和纵容,让他有了性格,并且很独特很有趣,牢牢占据了作品的中心。有时是通过对话,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向前发展;有时是不给人物太多的说话机会,主要是用行动这个“无声的语言”,侧重于写人物的动作。他笔下的人物,如毓贤、贾博尔等即使好像是反面人物也是具有多面性的,就像生活本身一样。
作家使用了一种经过他自己虚构的,只用来在心中默读的特别的言说方式,他的语言是有轻重、速度、色彩和气息的。书中到处闪现着万德生、罗莉莎等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及耸肩摊手的洋人形象,带来了钟楼、教堂、广智院、基督剧、壁炉、福音婢女、万民托命、“扛着福音去陕西”等载体和“西式文娱”,在平头百姓生活中加进了一些“西味”。晚清民国时期,柠州如同中国地方社会“国逢有事之秋,民遭涂炭之年”,书中出现了“青楼”、“小兰花女”、“七姨太”、“炸口弹”、“三寸金莲”、“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等民间俗语。以峪道河为地域的乡村气息浓浓逼人,诸如贾笙、崔润田、黎新明这些大村镇里的小人物,看似寥寥数笔,可增可减,但是细读一下,少了哪一个也成就减了峪道河乡村的整体生气。在方言的熟练运用层面上,在与名人名作中贴着时代的语境的语言追求上相比,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一直是这部小说高扬的一面旗帜。
西方文化冲击着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以来又是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个底子一直在与西方文化碰撞,在碰撞中协调相容,在相容中发展自己。这部书有生机勃勃对中西合璧物质世界的描绘,也能从这个世界背后看到一条长长的崇尚改革、助推开放精神探索的影子。
书中涉及中外冯玉祥、万德生、罗瑞英、恒慕义、余心清、毕德生、恒安石、史迪威、费正清、林徽因、柯棣华和郭庆兰、凯瑟琳、周祥玉等有影响的人物,还有美国卡尔顿大学来铭义中学的国际友人,他们或风流倜傥,举足轻重,或叱咤风云,声振寰宇,都是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他们的出现使古柠州政治气候与寰球风云同频共振。
《丁香花开时》最见功力处在于小说的鸿篇架构与虚实结合,既有人物的塑造,也有故事情节的推动和细部描写,不能不说是中国百年来社会生活重要一隅的缩影,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这里还想谈的是,小说是做了一些细部描写,但描写的空间还可扩展。特别需要注意语言针脚的绵密。这个针脚就密布在小说的细节、人物的性格逻辑,甚至某些词语的使用中。同时也寄希望于作家笔下的人物再个性化一些。一个作家有很大的雄心和能力,就会塑造出与以往文学画廊里所有的“人物”都不一样的形象。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很难的。
本书作者马鸿宾是我在山西省中青年作家影视创作高级研修班授课时参加研修的一位学员,由此不仅是影视剧本创作,文学品赏与交流日臻甚频。得知他大作付梓,甚感欣慰。综观书稿,我觉得能出一部长篇特别是近几年是非常不易的,这些是我对这部作品的整体感知,愿作家在小说长篇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