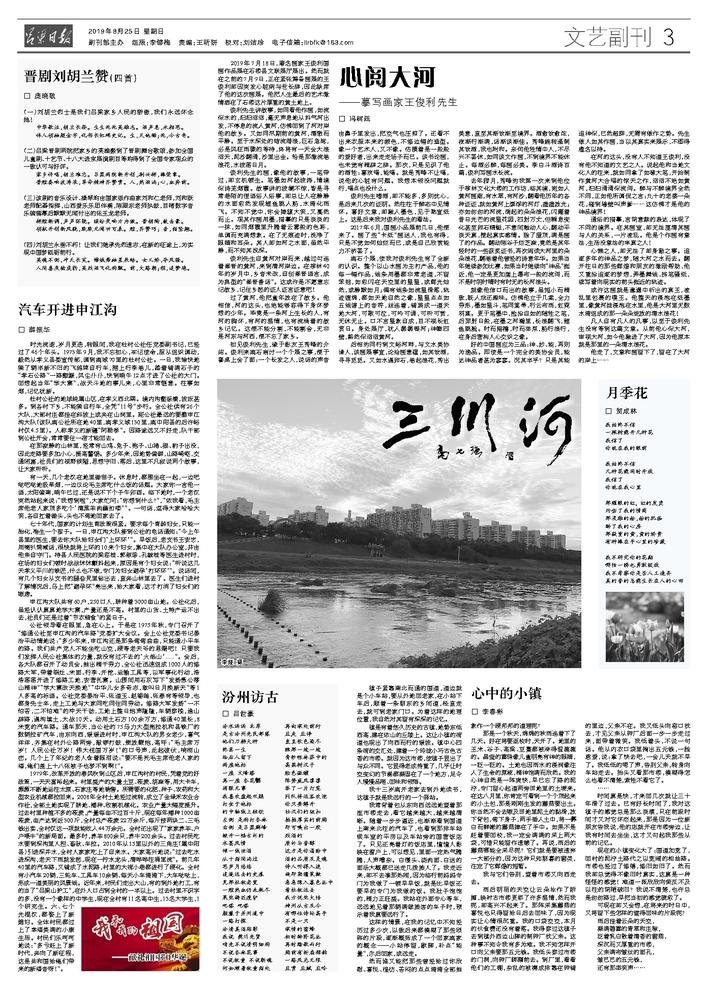镇子紧靠南北而通的国道,道边就是个小车站,要从外地回老家,在小站下车后,顺着一条朝东的乡间道,径直走去,就可到老家门口。为着这样的地理位置,我自然对其留有深深的记忆。
镇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地势东低西高,建在依山的丘陵上。这让小镇的街道也现出了向西而行的缓坡。镇中心四条街的交汇处,建着一个玲珑小巧古色古香的市楼。就因为这市楼,使镇子显出了与众不同。它显得老成持重了,几乎让时空变幻的节奏都凝固在了一个地方,足令人慢慢品咂、回味和领悟。
我十三岁离开老家去到外地读书,这镇子就是我远行的一个驿站。
我常背着包从东向西远远地望着那座市楼走去,看它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随着一步步逼近,也渐渐看到国道上南来北往的汽车了,也看到那排车站候车室的平房以及车站旁的国营饭店了。只见还亮着灯的饭店里,憧憧人影映在窗户上,可以想见,里面一定热气腾腾,人声嘈杂。白馒头、浇肉面、白送的面汤大概都已送走几拨旅人了。我走近来,却不去凑那热闹,因为临行前妈妈专门为我做了一顿早早饭,就是比早饭还要早的专门为我做的饭。我肚子饱饱的,精力正旺盛。我站在外面专心等车,远远地见着那辆满载旅客的车子时,预示着我真要远行了。
这样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以致后来都模糊了那些琐碎的片段,逐渐概括成了一个回家离家的概念——小站停留,歇脚,补点“能量”,尔后回家,或远走。
然而谁又能把那些曾经给过你欣慰、喜悦、徨彷、苦闷的点点滴滴全部抽象作一个硬邦邦的道理呢?
那是一个秋天,绵绵的秋雨连着下了几天。好在将要返校时,天开了。地里的玉米、谷子、高粱、豆蔓都被淋得湿漉漉的。晶莹的露珠像儿童明亮有神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土地也因雨水的浸润像注入了生命的原液,精神饱满而欣然。我的心神自然是一阵爽快,早已忘了路的泥泞,专门留心起道两旁田地里的土埂来。在这八月里,你肯定可看到一个个顶起来的小土包,那是刚刚生发的蘑菇要出土。你当然不会去顾及田地里泥土的黏滑,放下背包,弯下身子,两手插入土中,将一公式白而鲜嫩的蘑菇捧在了手中。如果不是赶着要回校,我一定会满满的采上两大袋,可惜只能留作遗憾了。再说,雨后的蘑菇哪能全采尽呢?它们就是要被遗弃一大部分的,因为这种只知朝暮的菌类,注定了它辉煌的短暂。
我与它们告别,望着市楼又向西走去。
雨后明丽的天空让云朵妆作了娇媚,映衬古市楼更添了许多温情,然而我呢,却高兴不起来了。那阵采集蘑菇的喜悦也只得留给日后去回味了,因为现实让心情很沉重。我的口袋空空,本月的伙食费还没有着落。我得穿过这镇子去到镇外西边山脚的制砖厂找父亲。这种事不知令我有多为难。我不知怎样开口向父亲要那五元钱。我低头穿过市楼的门洞,向砖厂踯躅前去。到厂里,看看他们的工棚,杂乱的被褥成排靠在砖铺的里边,父亲不在。我又低头向窑口找去,才见父亲从砖厂后面一步一步走过来,面带着微笑。我低着头,不说一句话。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五元钱,一脸慈爱,说:拿了快去吧,一会儿天就不早了。我低低的嗯了声,告别父亲,转身向车站走去。抬头又看那市楼,模糊得怎么也看不清楚,索性不看它了。
……
时间真是快,才来回几次就让三十年滑了过去。已有好长时间了,我对这镇子的感觉总是那么淡漠,只在前段时间才又对它怀恋起来,那是因为一位新朋友告我说,他的店就开在市楼旁边,让我有时间去坐坐,这才又勾起我那些从前的记忆。
现在的小镇变化大了:国道加宽了,回村的泥泞土路代之以宽阔的柏油路。市楼也经过了修缮,修旧如旧了。然而我却总觉得不像旧时真实,这真是一种怪怪的感觉!难道一派欣欣向荣反不及以往的简陋破旧?我说不清楚,也许总是匆匆路过,早把当初的感觉疏忽了。
可现在却又会想,在将来的时日中,又将留下些怎样的值得回味的片段呢?
雨后挂着云朵的天空,
凝满碧露的青草和庄稼,
泛着乳白散着清香的菌菇,
深沉而又厚重的市楼,
父亲满布皱纹的面孔,
皱巴巴的五元钱,
还有那串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