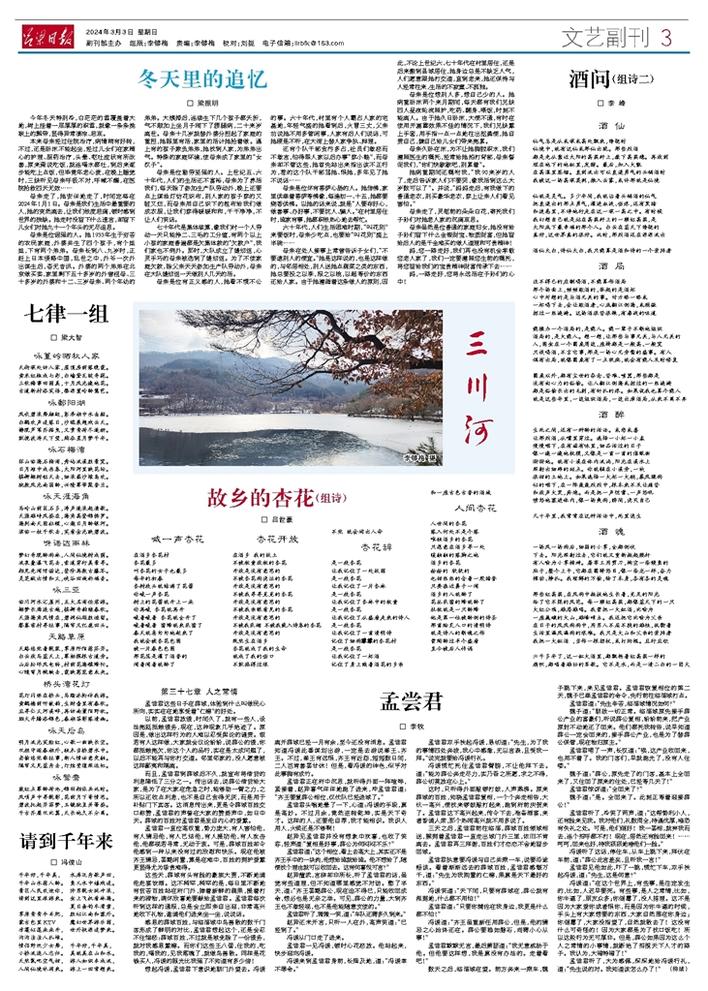今年冬天特别冷,白茫茫的雪覆盖着大地,树上挂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就像一条条挽联上的飘带,显得异常凄凉、悲哀。
本来母亲经过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不过,还是卧床不能起坐,经过儿女们在家精心的护理、服药治疗,头晕、呕吐症状有所改善,原来甭说吃饭,就连喝水都吐,到后来逐步能吃上点饭,但毕竟年老心衰,在晚上睡觉时,三妹听见母亲呼吸不对,呼喊不醒,在医院抢救四天无效……
母亲走了,她安详地走了,时间定格在2024年1月1日。母亲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她的突然离去,让我们极度悲痛,顿时感到世界的残缺。她走时没留下什么遗言,却留下儿女们对她九十一个年头的无尽追思。
母亲是位倔强的人。她1933年生于穷苦的农民家庭,外婆共生了四个孩子,有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母亲长到八、九岁时,正赶上日本侵略中国,乱世之中,外爷一次外出谋生后,杳无音讯。外婆的两个弟弟在北京做买卖,家里剩下五十多岁的外曾祖母、三十多岁的外婆和十二、三岁母亲、两个年幼的弟弟。大姨婚后,连续生下几个孩子都夭折,气不顺加上坐月子闹下了腰腿病,二十来岁离世。母亲十几岁就替外婆分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她眼里有活,家里的活计她抢着做。遇上有的孩子欺负弟弟,她找到人家,为弟弟出气。特殊的家庭环境,使母亲成了家里的“女汉子”。
母亲是位勤劳坚强的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生活还不富裕,母亲为了养活我们,每天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外,晚上还要点上煤油灯纺花织布,别人家的孩子穿的又脏又烂,而母亲用自己织下的粗布给我们做成衣服,让我们穿得暖暖和和,干干净净,不让人们笑话。
七十年代是集体核算,像我们村一个人劳动一天只能挣二、三毛的工分值,有两个以上小孩的家庭普遍都是欠集体款的“欠款户”,我们家也不例外。那时,大队成立了缝纫组,心灵手巧的母亲被选到了缝纫组。为了不使家庭欠款,除父亲天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外,母亲在大队缝纫组一天做别人几天的活。
母亲是位有正义感的人,她看不惯不公的事。六十年代,村里有个人霸占人家的宅基地,年轻气盛的她看到后,火冒三丈,父亲劝说她不用多管闲事,人家有后人们说话,可她硬是不听,在大街上替人家争执、辩理。
还有个队干部贪污多占,社员们敢怒而不敢言,怕得罪人家以后办事“穿小鞋”,而母亲却不管这些,她首先站出来指出该不正行为,惹的这个队干部骂她、恨她,多年见了她不说话……
母亲是位怀有菩萨心肠的人。她信佛,家里供奉着菩萨等佛像,每逢初一、十五,她都要烧香供佛。以她的话来说,就是“人要存好心,做善事、办好事,不要坑人、骗人。”在村里居住时,谁家有事,她都积极热心地去帮忙。
六十年代,人们生活困难时期,“叫花则”来要饭时,母亲少吃点,也要给“叫花则”盛上半碗……
母亲在处人接事上常曾告诉子女们,“不要逮别人的便宜。”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与邻居相处,别人送她点蔬菜之类的东西,她总要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以超等价的东西还给人家。由于她遵循着这条做人的原则,因此,不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村里居住,还是后来搬到县城居住,她身边总是不缺乏人气,人们愿意跟她打交道,直到老来,她还保持与人经常往来,生活的不寂寞、不孤独。
母亲是位想别人多,想自己少的人。她病重卧床两个来月期间,每天都有我们兄妹四人昼夜轮流照护,吃药、翻身、喂饭,时刻不能离人。由于她久日卧床,大便不通,有时在使用开塞露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我们兄妹戴上手套,用手指一点一点地往出抠粪便,她自责自己,嫌自己给儿女们带来拖累。
母亲久卧在床,为不让她胸腔积水,我们遵照医生的嘱托,经常给她拍打背部,母亲督促我们,“你们快歇歇吧,别累着”。
她病重期间还嘱咐我,“我90来岁的人了,走后告诉家人们不要哭,像我活到这么大岁数可以了”。并说,“妈妈走后,有我做下的普通老衣,别买豪华老衣,穿上让亲人们看见害怕。”
母亲走了,灵柩前的朵朵白花,寄托我们子孙们对她老人家的沉痛哀思。
母亲虽然是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她没有给子孙们留下什么金银财宝、物质财富,但她留给后人的是千金难买的做人道理和可贵精神!
妈,您一路走好,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孝敬您老人家了,我们一定要遵照您生前的嘱托,将您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妈,一路走好,您将永远活在子孙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