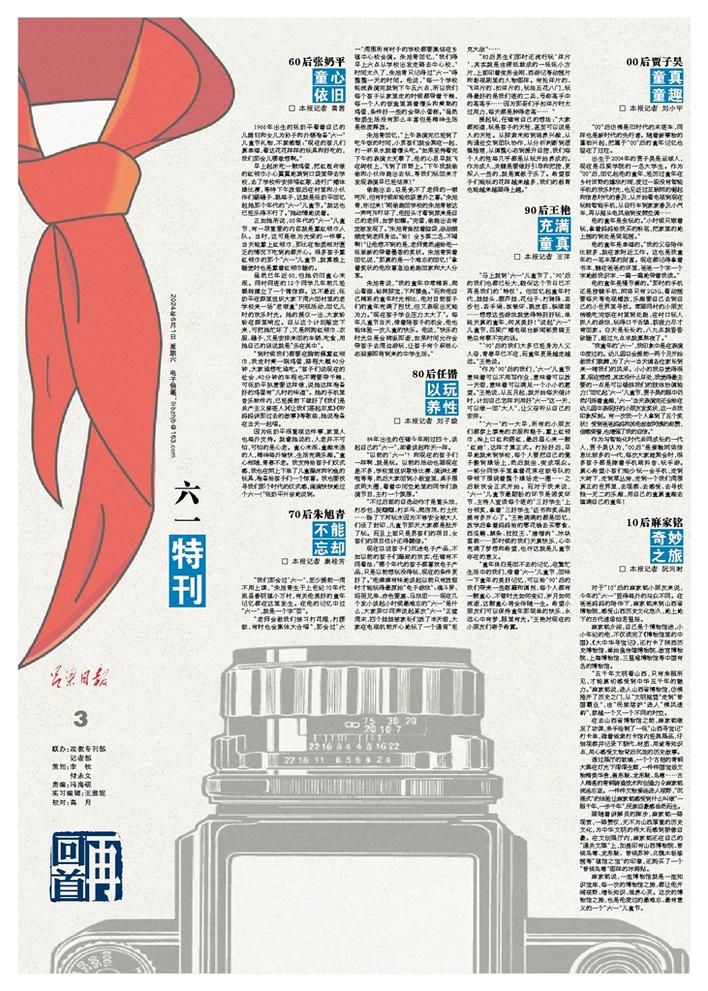60后张奶平
童心依旧
□ 本报记者 高茜
1966年出生的张奶平看着自己的儿媳妇和女儿为孙子和外甥准备“六一”儿童节礼物,不禁感慨:“现在的孩儿们真幸福,看这花花样样的玩具和好吃的,我们那会儿哪敢想啊。”
早上起床吃一颗鸡蛋,把红粗布做的红领巾小心翼翼地装到口袋里带去学校,去了学校听安排唱红歌、进行广播体操比赛,等待下午放假后在村里和小伙伴们踢毽子、跳格子,这就是张奶平回忆起她那个年代的“六一”儿童节。“就这也已经乐得不行了。”她动情地说着。
正如她所说,60年代的“六一”儿童节,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戴红领巾入队。当时,这可是极为光荣的一件事。当天能戴上红领巾,那比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吃到肉都开心。很多孩子戴红领巾的那个“六一”儿童节,就算晚上睡觉时也是戴着红领巾睡的。
虽然已年近60,但她仍旧童心未泯。同村同班的12个同学几年前几经辗转建立了一个微信群。这不最近,张奶平在群里组织大家下周六回村里的老学校来一场“老顽童”庆祝活动,回忆儿时的欢乐时光。她的提议一出,大家纷纷在群里响应。自从这个计划敲定下来,可把她忙坏了,又是网购红领巾、衣服、毽子,又是安排来回的车辆、吃食,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乐在其中”。
“到时候我们都要在胸前佩戴红领巾,我走时煮一锅鸡蛋,路程大概40分钟,大家谁想吃谁吃。”孩子们说现在的社会,40分钟的车程也不需要带干粮,可张奶平执意要这样做,说她这样准备好的鸡蛋有“儿时的味道”。她的手机里音乐软件内,已经提前下载好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等歌曲,她说准备在当天一起唱。
因为张奶平很重视这件事,家里人也格外支持。就像她说的,人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老。童心未泯、童趣未退的人,精神格外愉快,生活充满乐趣。“童心相随,青春不老。我支持给孩子们仪式感,我也在网上下单了儿童蹦床和钓鱼的玩具,准备给孩子们一个惊喜。我也要找寻我们那个时代的仪式感,痛痛快快地过个六一!”张奶平兴奋地说到。
70后朱旭青
不能忘却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我们那会过‘六一’,至少提前一周不用上课,”朱旭青生于上世纪70年代岚县普明镇小万村,有关他美好的童年记忆都在这里发生。在他的记忆中过“六一”,就是一个字“耍”。
“老师会教我们练习打花棍,打腰鼓,有时也会集体大合唱”,那会过‘六一’周围所有村子的学校都要集结在乡镇中心校会演。朱旭青回忆,“我们得早上六点从学校出发走路去中心校,”时间太久了,朱旭青只记得过“六一”得整整一天的时间。他说,“每一个学校轮流表演完就到下午五六点,所以我们每个孩子从家里走的时候都带着干粮,每一个人的饭盒里装着馒头和煮熟的鸡蛋,条件好一些的会带小蛋糕。”虽然物质生活没有那么丰富但是精神生活是极度释放。
朱旭青回忆,“上午表演完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小男孩们就会聚在一起,打一杯泉水就着馒头吃。”如果坚持看完下午的表演太无聊了,他的心思早就飞在树枝上,飞到了田野上。“下午我就偷偷和小伙伴跑出去玩,等我们玩回来才发现表演早已经结束!”
偷跑出去,总是免不了老师的一顿呵斥,但有时候却能收获意外之喜。“朱旭青,你过来!”刚偷跑回学校的朱旭青被这一声呵斥吓坏了,他扭头才看到原来是自己的老师,如梦初醒。“完蛋,偷跑出去肯定被发现了。”朱旭青耷拉着脑袋,战战兢兢走到老师身边。“给!全乡第二名,不错啊!”让他想不到的是,老师竟然递给他一张崭新的带着墨香的奖状。朱旭青笑着回忆说,“那真的是一个难忘的回忆!”拿着奖状的他欣喜急迫地跑回家和大人分享。
朱旭青说,“我的童年非常精彩,爬山看狼、钻洞探宝,下河摸鱼。”而和他自己精彩的童年时光相比,他对目前孩子们的童年充满了担忧,但又表现出无能为力。“现在孩子学业压力太大了”。每年儿童节当天,借着陪孩子的机会,他也能体验一次儿童的快乐。他说,“快乐的时光总是会稍纵即逝,如果时间允许会带孩子去周边游玩,让孩子有个积极心态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
80后任锴
以玩养性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84年出生的任锴今年刚过四十,谈起自己的“六一”,却像谈起昨天一样。
“以前的‘六一’?和现在的孩子们一样啊,就是玩。以前的活动也跟现在差不多,学校里组织歌咏比赛、演讲比赛啦等等,然后大家回到小教室里,桌子围成两大圈,看着中间空地里的同学们表演节目,主打一个氛围。”
“不过后面的自选动作才是重头戏,打沙包、捉蝈蝈、打乒乓、爬房顶、打土仗……除了下河玩水因为不够安全被大人们设了封印,儿童节那天大家都是扯开了玩。而且上面只是男孩们的项目,女孩们的项目估计还得翻倍。”
现在总说孩子们沉迷电子产品,不如以前的孩子们蹦跶的欢实,任锴有不同看法:“哪个年代的孩子都喜欢电子产品,只是以前想玩没得玩,现在的条件更好了。”他津津有味地谈起以前只有放假时才能玩得最原始“电子游戏”:魂斗罗、玛丽兄弟、赤色要塞、马戏团……现在几个发小谈起小时候最难忘的“六一”是什么,大家异口同声说起某次“六一”正值周末,四个娃娃被家长们放了半天假,大家在电视机前开心地玩了一个通宵“坦克大战”……
“80后男生们那时还流行玩‘洋片’,其实就是由硬纸裁成的一张张小方片,上面印着变形金刚、西游记等动画片和影视剧里的人物图样。有抡洋片的、飞洋片的、扣洋片的,玩法五花八门,玩得最好的是我们班的二兵,号称高手中的高高手……因为那哥们手扣洋片时太过用力,每天都是肿得老高…… ”
提起玩,任锴有自己的想法:“大家都知道,玩是孩子的天性,甚至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从探索未知到培养兴趣,从沟通社交到团队协作,从分析判断到逻辑推理,从调整心态到提升自控,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几乎都是从玩开始养成的。作为成人,关键是要做好引导和把控,更深入一些的,就是寓教于乐了。希望孩子们能玩的花样越来越多,我们的教育也能越来越跟得上趟。”
90后王艳
充满童真
□ 本报记者 王洋
“马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90’后的我们也都已长大,貌似这个节日已不再是我们的‘特权’。但回忆起童年时代,娃娃头、葫芦娃、花仙子、打弹珠、丢沙包、丢手绢、滚铁环、跳皮筋、躲猫猫……想想这些游戏就觉得特别好玩,单纯天真的童年,何其美好!”说起“六一”儿童节,吕梁广播电视台新闻部责编王艳总有聊不完的话。
“‘90’后的我们大多已经身为人父人母,青春早已不在,而童年更是越走越远。”王艳说。
“作为‘90’后的我们,‘六一’儿童节意味着可以不用写作业,意味着可以放一天假,意味着可以满足一个小小的愿望。”王艳说,从五月起,就开始每天倒计时,计划自己怎样利用好“六一”这一天,可以做一回“大人”,让父母听从自己的安排。
“‘六一’的一大早,所有的小朋友们都穿上漂亮的衣服和鞋子,戴上红领巾,涂上口红和腮红,最后眉心来一颗‘红痣’,这样才算正式。打扮好后,早早地就来到学校,每个人要把自己的凳子搬到操场上,然后就坐,变成观众。一部分同学手里拿着花束在鼓号队的带领下围绕着整个操场走一圈……之后联欢会正式开始。而对于我来说,‘六一’儿童节最期盼的环节是颁奖环节,主持人宣读每个班的‘三好学生’上台领奖,拿着‘三好学生’证书和奖品别提有多开心了。”王艳满满的都是回忆,放学后拿着妈妈给的零花钱去买零食、西瓜糖、辣条、拉拉王、“唐僧肉”、冰块雪糕……那时候的我们天真快乐,心中充满了梦想和希望,也许这就是儿童节存在的意义。
“童年终归是回不去的记忆,在繁忙生活中的我们,借着‘六一’儿童节,回味一下童年的美好记忆,可以给‘90’后的我们带来一些慰藉和调剂,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不管时光如何变幻,岁月如何流逝,这颗童心将会伴随一生。希望小朋友们可以保持童年那简单的快乐,永远心中有梦,眼里有光。”王艳对现在的小朋友们寄予希冀。
00后贾子昊
童真童趣
□ 本报记者 刘小宇
“00”后仿佛是旧时代的末班车,同样也是新时代的先行者。随着新事物的蓬勃兴起,把属于“00”后的童年记忆也留在了过往。
出生于2004年的贾子昊是运城人,现在是吕梁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作为“00”后,回忆起他的童年,经历过童年在乡村田野的嬉戏打闹,度过一段没有智能手机的欢乐时光,也见证过互联网的崛起和信息时代的普及,从开始看电视到现在玩转智能手机,从自行车到家家普及小汽车,再从摇头电风扇到变频空调……
他的童年是贪玩的。“小时候只顾着玩,拿着妈妈给我买的粉笔,把家里的地上画的到处是简笔画。”
他的童年是幸福的。“我的父母陪伴比较多,就在家附近工作。这也是我童年的一笔丰厚的财富。现在都记得拿着书本,躺在爸爸的怀里,爸爸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识字,一篇一篇地带着我读。”
他的童年是慢节奏的。“那时的手机还是按键手机,网络只有2G3G,看动画要每天等电视播放,乐趣要自己去到自己的小世界里寻找。常跟同村的小朋友傍晚吃完饭在村里到处跑,在村口玩人抓人的游戏,玩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才肯回家。白天是长长的,八九点就昏昏欲睡了,超过九点半就算熬夜了。”
“我童年的‘六一’,我印象中是在表演中度过的。幼儿园总会提前一两个月开始教我们跳舞,为了六一当天请各位家长到来一睹我们的风采。小小的我总觉得很累,现在想想,其实没什么坏处,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可以锻炼我们的肢体协调能力!”回忆起‘六一’儿童节,贾子昊的眼中仍然闪烁着童趣,‘六一’当天表演完还会给在幼儿园中表现好的小朋友发奖状,这一点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一个人拿到了五个奖状!受到爸爸妈妈和其他叔叔阿姨的称赞,倍感荣誉,也增强了我的自信。”
作为与智能化时代共同成长的一代人,贾子昊认为,“00后”是接触网络信息比较多的一代,每次大家庭聚会时,很多孩子都是捧着手机刷抖音、玩手游。真心希望小孩们能少玩一会手机,走到大树下,走到草丛旁,走到一个我们周围真正的世界里,去观察、去感受、去寻找独一无二的乐趣,用自己的童真童趣去填满自己的童年!
10后麻家铭
奇妙之旅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对于“10”后的麻家铭小朋友来说,今年的“六一”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麻家铭来到山西省博物院,感受山西历史文化悠久,地上地下的古代遗珍灿若星辰。
麻家铭介绍,自己是个博物馆迷,小小年纪的他,不仅读完了《博物馆里的中国》、《大中华寻宝记》,还打卡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中国有名的博物馆。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只有亲眼所见,才能真切感受到中华五千年的魅力。”麻家铭说,进入山西省博物馆,仿佛推开了历史之门,从“文明摇篮”走到“晋国霸业”,由“民族熔炉”进入“佛风遗韵”,穿越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时空。
在去山西省博物馆之前,麻家铭做足了功课,亲手绘制了一张“山西寻宝记”打卡单,循着线索打卡馆内经典展品,仔细观察并记录下朝代、材质、用途等知识点,用心感受文物背后沉淀的历史故事。
透过展厅的玻璃,一个个古拙的青铜大鼎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一件件国宝级文物精美华贵,兽形觥、龙形觥、鸟尊……古人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创造力令麻家铭流连忘返。一件件文物接连进入视野,“沉浸式”的体验让麻家铭感受到什么叫做“一眼千年,一步千年”,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麻家铭一路观赏,一路赞叹,无不为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为中华文明的伟大而感到骄傲自豪。在文创展厅内,麻家铭还在自己的“通关文牒”上,加盖印有山西博物院、晋侯鸟尊、龙形觥、 晋侯苏钟、北魏木板漆画等“镇馆之宝”的印章,还购买了一个“晋侯鸟尊”图样的冰箱贴。
麻家铭说,一座博物馆就是一座知识宝库,每一次的博物馆之旅,都让他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滋养心灵。这次的博物馆之旅,也是他度过的最难忘、最有意义的一个“六一”儿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