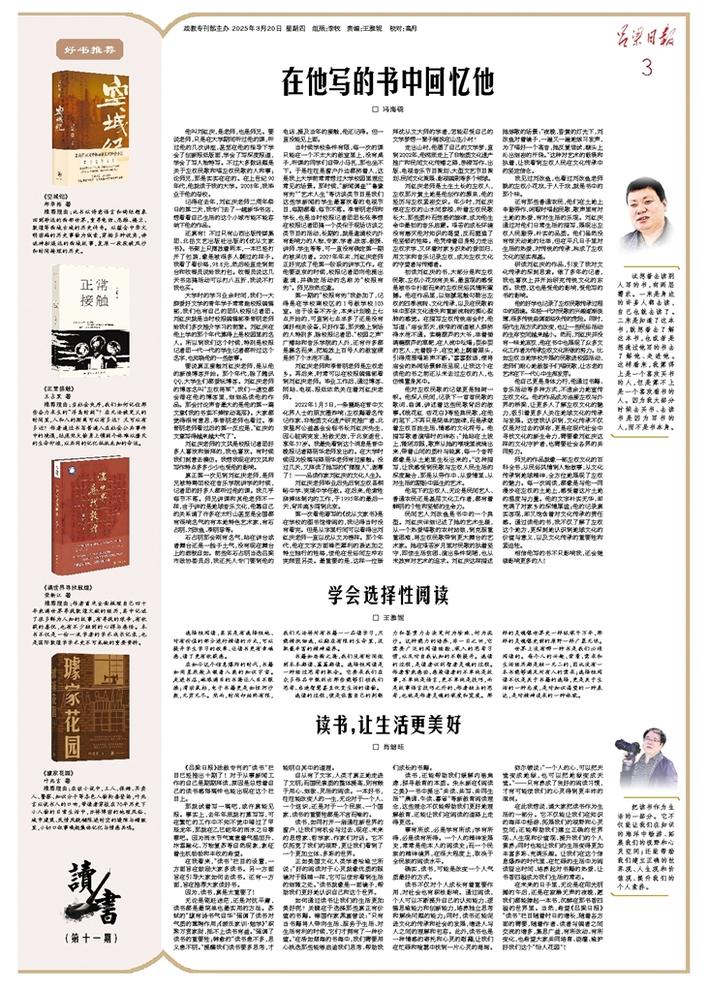试想着去读别人写的书,有两层需求。一来是身边的许多人都去读,自己也就去读了。二来是知道了这本书,就想着去了解这本书,也或者是想通过他写的书去了解他、走进他。这样看来,我算得上是一个喜欢买书的人,但是算不上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因为我大部分时候去买书、去读书是因为写书的人,而不是书本身。
他叫刘红庆,是老师,也是师兄。要说老师,只是在大学期间听过他的课,听过他的几次讲座,甚至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创新报纸版面,学会了写深度报道,学会了写人物特写。不过大多数话题是关于左权民歌和唱左权民歌的人和事;论师兄,那是实实在在的。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读于我的大学。2008年,我毕业于他的母校。
记得在去年,刘红庆老师二周年祭日的第二天,我专门去了一趟新华书店,想看看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城市能不能容纳下他的作品。
还真有!不过只有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家书》。书架上只摆放着两本,一本已经打开了包装,像是被很多人翻过的样子。我看了看价格,98.8元,然后径直走到前台和收银员说给我打包。收银员说这几天书店搞活动可以打八五折,我说不打我也买。
大学时的学习业余时间,我们一大群爱好文学的青年学子常常跑校报编辑部,我们也有自己的团队校报记者团。刘红庆就是当时校报编辑部李晋明老师给我们多次推介学习的前辈。刘红庆在他上学的那个年代算得上是校园里的名人。所以到我们这个时候,特别是校报记者团一代一代的学生记者都听过这个名字,也知晓他的一些故事。
要说真正接触刘红庆老师,是从他的新浪博客开始。那个年代,除了腾讯QQ,大学生们都爱玩博客。刘红庆老师的博客名叫“左权将军”,我们一逮空都会潜在他的博客里,细细品读他的作品。那会讨论声音最大的是他的第一篇文章《我的书卖不掉惊动高层》。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李晋明老师也看过。李晋明老师看过后的第一反应是,“红庆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大气了”。
刘红庆老师的文风是校报记者团好多人喜欢和崇拜的,我也喜欢。有时候我们刻意去模仿。我想我现在的文风和写作特点多多少少也受他的影响。
真正第一次见到刘红庆老师,是师兄被特聘回校在音乐学院讲学的时候,记者团的好多人都听过他的课。我几乎每节不落。师兄讲课和其他老师不一样,由于讲的是地域音乐文化,他靠自己的关系请了许多在太行山甚至是全国都有很响名气的有本地特色艺术家,有石占明、刘改鱼、李明珍等。
石占明那会刚有名气,站在讲台或者舞台还是一脸子土气,没有现在舞台上的洒脱自如。前些年石占明当选吕梁市政协委员后,我还托人专门要到他的电话,提及当年的接触,他还记得。但一直没能见上面。
当时候学校条件有限,每一次的课只能在一个不太大的教室里上,没有桌子,听课的同学们自带小马扎,那也坐不下。于是往往是窗户外边都挤着人,这是我上大学前常常想过大学校园里理应常见的场景。那时候,“新闻调查”“鲁豫有约”“艺术人生”等访谈类节目是我们这些学新闻的学生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每期都看、每节不落。李晋明老师和学长,也是当时校报记者团团长张亭想在校报记者团搞一个类似于现场访谈之类节目的活动,长期的,就是邀请校内外有影响力的人物,专家、学者、政客、教授、讲师、学生等等,可一直没有确定第一期的被采访者。2007年年末,刘红庆老师正好完成了他第一阶段的讲学工作。在他要返京的时候,校报记者团向他提出邀请,并确定活动的名称为“校报有约”。师兄欣然应邀。
第一期的“校报有约”我参加了,记得是在学校南校区的1号教学校103室。由于设备不齐全,本来计划晚上七点开始的,可直到七点半多了还是没有调好相关设备,只好作罢,那天晚上到场的人特别多,除校报记者团、“校园之声”广播站和音乐学院的人外,还有许多都是慕名而来,把能放上百号人的教室硬是挤了个水泄不通。
刘红庆老师和李晋明老师是左权老乡。再后来,时常可以在校报编辑部看到刘红庆老师。毕业工作后,通过博客、网站、电视、报纸依然关注着刘红庆老师。
2022年1月5日,一条噩耗在晋中文化界人士的朋友圈炸响:左权籍著名传记作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推广者、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红庆先生,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57岁。我最先看到这个消息是晋中晚报记者路丽华老师发出的。在大学时候因为投稿与路丽华老师有过接触。没过几天,又拜读了她写的《“摆渡人”,谢幕了!——品读作家刘红庆的文化人生》。
刘红庆老师毕业后先后到左权县桐峪中学、突堤中学任教。在后来,他索性辞掉体制内的工作,于1995年的最后一天,背井离乡闯到北京。
第一次看他著写的《沈从文家书》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借阅的,我记得当时没有看完。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刘红庆老师一直以沈从文为榜样。那个年代,他在文字方面锋芒犀利的表达加之特立独行的性格,使他在世俗间左冲右突颇显另类。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位崇拜沈从文大师的学者,怎能忍受自己的文学梦想一辈子搁浅在山庄小村?
走出山村,他圆了自己的文学梦,直到2002年,他彻底走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和民间文化传播之路,涉猎写作、出版、电视音乐节目策划、大型文艺节目策划、民间文化策展、影视编剧等多个领域。
刘红庆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左权人,左权那片黄土地是他创作的源泉,他的经历与左权紧密交织。年少时,刘红庆便在左权的山水间穿梭,听着左权民歌长大,那些质朴而悠扬的旋律,成为他生命中最初的音乐启蒙。艰苦的成长环境没有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望,反而塑造了他坚韧的性格。他凭借着自身努力走出左权求学,又怀着对家乡炽热的爱回归,用文字和音乐记录左权,成为左权文化的守望者与传播者。
初读刘红庆的书,大部分是和左权民歌、左权小花戏有关系,最直观的感受是被书中扑面而来的左权民俗风情所震撼。他在作品里,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左权的四季流转、文化传承,以及在民歌韵味中那抹文化遗失和重新流转的撕心裂肺的感觉。在描写左权传统庙会时,他写道:“庙会那天,狭窄的街道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卖糖葫芦的大爷,举着插满糖葫芦的草靶,在人流中吆喝;耍杂耍的艺人,光着膀子,在空地上翻着跟头,引得周围喝彩声不断。”寥寥数语,便将庙会的热闹场景鲜活呈现,让我这个在读他的书之前还从未去过左权的人,也仿佛置身其中。
他对左权民歌的记载更是独树一帜。他深入民间,记录下一首首民歌的歌词、曲调,讲述着这些民歌背后的故事。《桃花红 杏花白》等经典民歌,在他的笔下,不再只是简单的旋律,而是承载着左权百姓生活、情感的文化符号。他描写歌者演唱时的神态:“她站在土坡上,微闭双眼,歌声从她的喉咙里流淌出来,带着山间的质朴与纯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这种描写,让我感受到民歌与左权人民生活的深度融合,那是从劳作中、从爱情里、从对生活的期盼中诞生的艺术。
他笔下的左权人,无论是民间艺人、普通农民还是基层文化工作者,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坚韧的生命力。
民间艺人刘改鱼是书中的一个典型。刘红庆详细记述了她的艺术生涯,从一个热爱唱歌的农村姑娘,到克服重重困难,将左权民歌带到更大舞台的艺术家。她在艰苦岁月里对民歌的执着坚守,即使生活贫困、演出条件简陋,也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刘红庆这样描述她练歌的场景:“夜晚,昏黄的灯光下,刘改鱼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发声,为了唱好一个高音,她反复尝试,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这种对艺术的敬畏和执着,让我看到左权人民在文化传承中的坚定信念。
我见过刘改鱼,也看过刘改鱼老师跳的左权小花戏,于人于戏,就是书中的那个味。
还有那些普通农民,他们在土地上辛勤劳作,闲暇时唱起民歌,歌声里有对土地的热爱,有对生活的乐观。刘红庆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出左权人民勤劳、朴实的品质。他们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在平凡日子里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传承,构成了左权文化的坚实根基。
研读刘红庆的作品,引发了我对文化传承的深刻思索。做了多年的记者,我也喜欢上并开始研究传统文化的东西。我想,这也是受他的影响,受他写的书的影响。
他的好学也记录了左权民歌传承过程中的困境。年轻一代对民歌的兴趣逐渐淡薄,很多传统曲调面临失传的危险。同时,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让一些民俗活动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然而,刘红庆并没有一味地哀叹,他在书中也展现了众多文化工作者为传承左权文化所做的努力。比如左权当地学校开展的民歌进校园活动,老师们耐心地教孩子们唱民歌,让古老的艺术在下一代心中生根发芽。
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通过书籍、音乐活动等多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左权文化。他的作品成为连接左权与外界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左权文化的魅力,吸引着更多人关注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使我认识到,文化传承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保存,更是在现代社会中寻找文化的新生命力,需要像刘红庆这样的文化守护者,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师兄的作品就像一部左权文化的百科全书,从民俗风情到人物故事,从文化传承到地域精神,全方位地展现了左权的魅力。每一次阅读,都像是与他一同漫步在左权的土地上,感受着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力量。他的文字朴实无华,却充满了对家乡的深情厚谊;他的记录真实客观,却又饱含着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通过读他的书,我不仅了解了左权这个地方,更深刻地认识到地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以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相信他写的书不只影响我,还会继续影响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