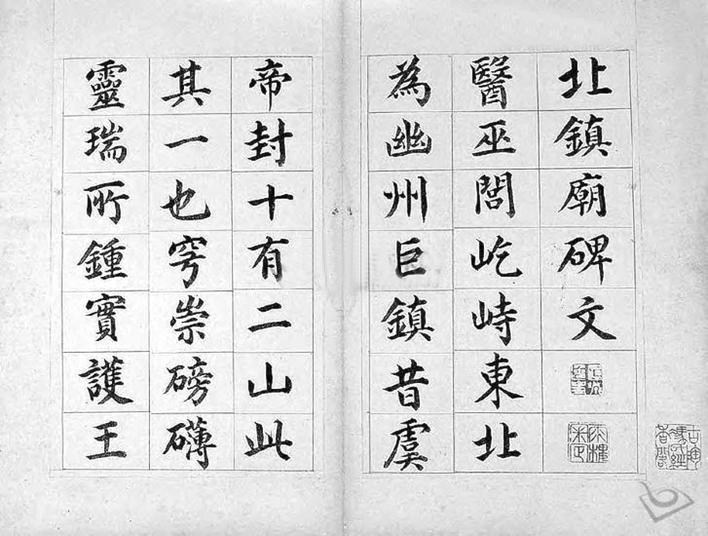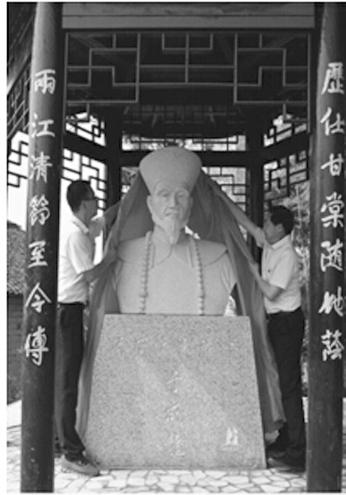铁面情面
一般来说,清官都是“铁面无私”的,但中国偏偏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能够没有“情面”。于成龙呢,一方面努力做到“铁面”,另一方面也努力想讲“情面”。《从好录》就记载了这么几个故事。
在歧亭的时候,曾经有一位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远道来访。此人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位仗义疏财、家道中落的“社友”。当初大家热情结社,以文会友,这位朋友仗着家里有钱,帮完这个帮那个,最后把自己家里那点钱给散完了。后来,社友们纷纷出仕做官,这位朋友也算是苦尽甘来,慨然接受朋友们的丰厚回报。这次,他来到歧亭,一方面是看望于成龙,另一方面是有私事要请托。于成龙是穷官,不可能赠给他大笔银子,但帮他办点事总可以吧?
于成龙见到老朋友,非常开心。虽然没有好酒好菜,但热情招待是必需的。喝完了酒,两人免不了还要促膝谈心,联床夜话,诉尽平生之情。但朋友一旦把话题向私情私事上引,于成龙马上就严肃起来,不是说“上帝临汝”,就是说“天监在兹”,意思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老天爷在上边看着,阎王爷在下边管着,还有什么“因果报应”“天理良心”……
结果,朋友想托付于成龙的私事,硬是没有机会说出来。朋友临走的时候,于成龙翻箱倒柜,东挪西借,凑了几两银子给朋友拿上。这朋友,估计只能是摇头叹息,拿于成龙一点办法也没有。朋友走了,于成龙却欠下饥荒,得饿几天肚子了。
另一件事:
某官宦人家的仆人,拔了别人田里的豆子,田主据理力争,这仆人又动手打了人。双方闹腾起来,告到了于成龙的官衙。这仆人知道于成龙和他家主人是好朋友,就领着家主一起来打官司。
于成龙说:“拔豆子虽然是件小事,但很多违法犯罪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不能不教训他一次。”说完,就命差役把这仆人拉下去打板子。打完之后,方和这家主人叙朋友交情,饮酒论诗,极尽风雅。
这人一大家子叔伯弟兄都是做官的,本人又与于成龙交好,但碰上于成龙这么个古怪朋友,他有什么办法?
署理武昌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虚岁五十八,可以称是年近花甲,完全算个老年人了。这一年,他最忙、最累、最委屈,也最光荣。《于清端公政书》这一年的记载也最丰富,很多事件都有具体的日期。
二月,他完成“入觐”任务,长途跋涉,从北京回到黄州。三月初,接到巡抚张朝珍的命令,调往武昌,“署理”武昌知府,办理军需事务。三月九日,他从黄州赶到武昌,履任新职。过了不久,吏部下了调令,升于成龙为福建省建宁府知府,巡抚张朝珍上报朝廷,要求就近改任于成龙为武昌知府。
每年四月,是清廷规定的征收赋税期限。武昌各县靠近战场,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战争。这年的赋税,是应该“开征”,还是“缓征”,湖广省的官员们有不同意见。于成龙是主张“缓征”的,他写了一篇《为武昌各属请缓征详》,介绍了蒲圻、嘉鱼、通城、咸宁、崇阳、大冶、兴国、武昌、通山、江夏等州县百姓流离失所、惊恐不定、无力务农的情况,表示征收实有困难,不如照旧“缓征”。
于成龙的这个建议是十分明智的。如果“开征”,最苦恼的是各地百姓,而最劳累的是各级官员。百姓没有收成,自然也没有钱粮可缴,逼急了就都投奔吴三桂去了。官员们的头等大事是办理军需,如果都跑去催征赋税,耽误了军需大事,那是要丢官掉脑袋的。如果“缓征”,既能安抚百姓,又能让官员们专心办理军需。所欠钱粮,可以在太平后补缴,或者向朝廷申请“蠲免”。
于成龙还写过一篇《请复临湘驿站详》,主要是请求湖广巡抚张朝珍移文给偏沅(湖南)巡抚,恢复临湘界内的几处驿站,方便军情通信。
崇贤兴教
“方山子”陈公式是麻城县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北宋时期隐居在歧亭镇的杏花村。大文豪苏东坡曾写过一篇《方山子传》,很传神地介绍了陈公式英雄侠气、折节读书、隐居修行的故事。于成龙在治盗之余,也想表彰先贤、教化百姓,就把陈公式当成了“典型”和“榜样”。
康熙十一年,于成龙主持修建了一座“宋贤祠”,在祠中祭祀纪念陈公式。同时,他又把“宋贤祠”办成了讲学的书院,召集本地的读书人,定期在祠中讲圣贤之道,弘扬汉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于成龙不仅为“宋贤祠”题写了“辉光照国”的匾额,还亲手在祠院中种植了两棵桂树。
于成龙夜间巡城时,一旦发现书馆里半夜亮着灯的,或有诵读之声的,他不是进去小坐一会儿,就是在第二天把那位夜读的士子请到衙门里交谈,极尽礼敬鼓励,因此和当地士子们建立了良好的师友关系。其中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后来一直和于成龙保持联系,在平定东山叛乱时为于成龙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成龙平生撰写的文稿,就是由黄州士子、著名学者李中素帮助整理的。
于成龙兴建“宋贤祠”大有深意。陈公式抛弃富贵功名,过着庵居蔬食、徒步往来、学佛修道的俭朴生活,和于成龙的人生追求是一样的。陈公式痛改“一世豪士”的习气,折节读书,安贫乐道,对强悍好斗、豪杰辈出的黄州百姓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于成龙希望百姓们都好好种田,好好读书,做良民百姓和清官廉吏,共同创造太平生活,千万别再去做什么绿林好汉。
二举“卓异”
于成龙做黄州府同知的四年之中,曾经有两次赴京“入觐”的经历。
地方官赴京“入觐”,按规定每三年一次,任务是到吏部述职,汇报工作,接受调查。运气好了,还可能受到皇帝的亲切接见或者提拔重用;运气不好,就会丢官降职。“入觐”的官员,包括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还有各府的“佐贰”官。因为知府责任重大,不能擅离,就把同知或通判这两个副职派一个去代劳。于成龙的两次“入觐”,可能还和“卓异”有关。
于成龙第一次“入觐”,是在康熙九年的早春。出发的时候天气还很冷,一路受尽风霜之苦,曾经写下了一首《纪行》诗。在北京过了端午节,写了一首《长安邸中午日》,感叹道:
十年浮萍宦异乡,回思已事倍神伤。
榴裙喷火红颜好,荷盖擎珠绿水凉。
泡雨有无呼吸变,奇云生灭古今忙。
悲歌慷慨当年梦,白发空惭续命长。
他上次赴京是顺治十八年,一晃十年就过去了。没有死在罗城、合州,还从正七品做到了正五品,侥幸之中自然是感慨万端。这次“入觐”,于成龙还得到了“蟒服冠带”的奖励,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于成龙第二次“入觐”是在康熙十三年春,往返时间很短,二月份便回来了。
这时候,他在黄州已经颇有政绩,在湖广省也有了能吏的名声。康熙十二年的时候,湖广总督蔡毓荣召见了他,赞誉有加。蔡总督见于成龙官服破旧,还很例外地赏了他一套新官服,这就是于成龙在几篇文章中提到的“赐章服”。在这一年的“大计”中,新上任的湖广巡抚张朝珍,根据于成龙的实际政绩,举他为“卓异”,这是于成龙第二次被举为“卓异”了。在清朝的官场上,举“卓异”是十分难得的荣誉,于成龙辛苦工作多年,努力行善多年,总算是有了回报,所谓“苦心人天不负”也。但这次“卓异”的评语,各种传记资料都没有记载,应该是失传了。
根据于成龙的一贯作风,他应该还有一些特别的举动和成绩,获得了总督蔡毓荣和巡抚张朝珍的青睐。就像在罗城和合州那样,他很可能向上级提供过不少合理化建议。另外,他在黄州府同知任期内,兼任过“黄汉捕务”,应该是全面管理黄州府和汉阳府的捕盗工作。陈廷敬的《于清端公传》中说他“摄汉阳、黄安、通城事”,也就是代理汉阳府、黄安县、通城县的政务,做过“绝火耗”“饬保甲”等工作。这说明,于成龙在黄州府同知任期内,已经引起湖广省高层官员的重视,被临时调动官职,负责了更多的工作,做出了更多的成绩。只是因为《于清端公政书·武昌书·黄州书》内容的严重缺乏,我们不能做更详细的介绍了。根据新发现的《于成龙墓志铭》残碑,当时通城县赋税拖欠严重,于成龙署理县务时,“诚心感劝”,百姓踊跃输纳,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赋税任务,清理了拖欠。因为这个特殊政绩,才被举为“卓异”。
于成龙第二次“入觐”应该是劳碌而愉快的旅程,到吏部述职后,朝廷核准了他的“卓异”,很快就下令升他为福建省建宁府知府,成为正四品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