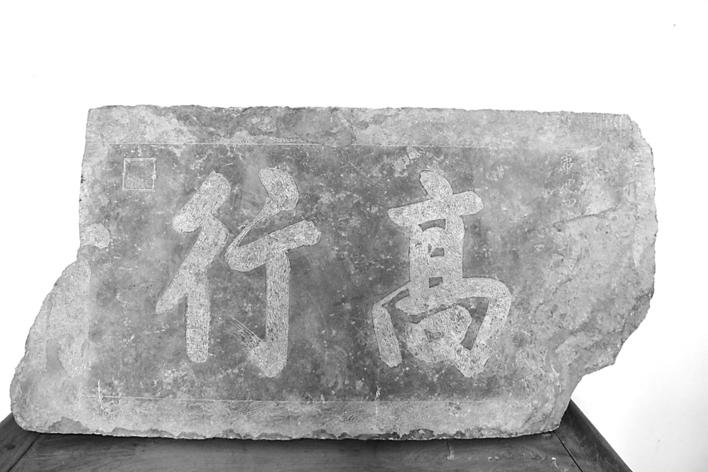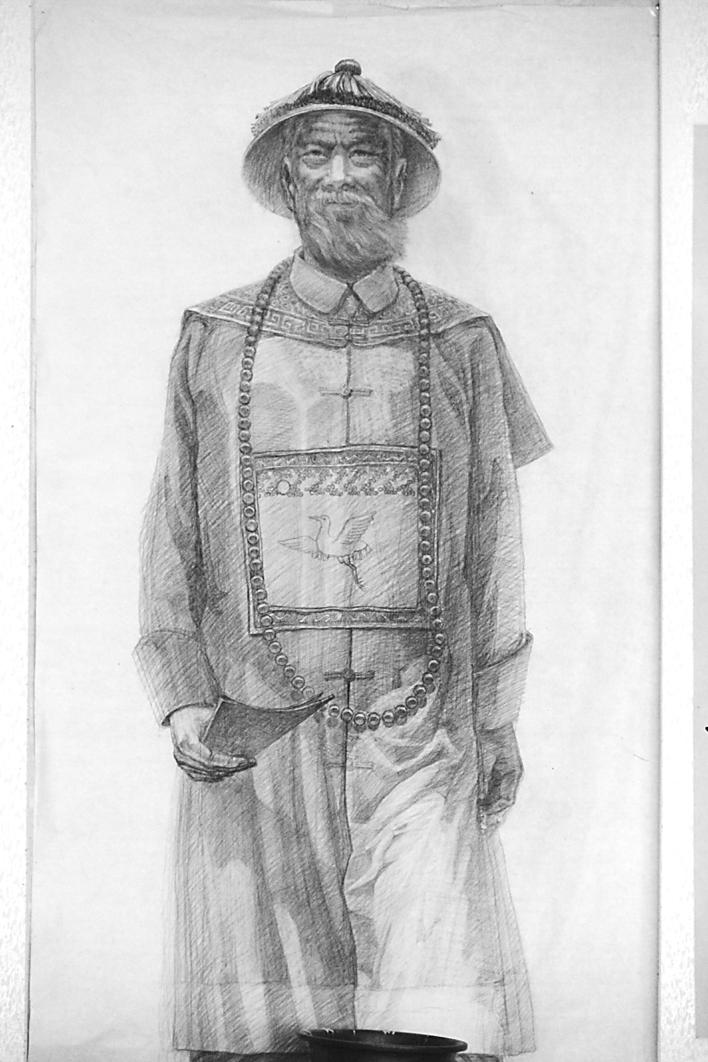能吏风范
于成龙在“署理武昌知府”的短暂日子里,还办了两件比较露脸的事情。
当时,清军云集于荆州、武昌、宜昌等地,面对吴三桂的强烈攻势,他们畏首畏尾,不敢争锋,但面对地方官吏和老百姓,他们又是另一副强横嘴脸。有一名“恶少”,借着军方的背景,在民间为非作歹,犯了罪就跑回军营,地方官吏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于成龙接到百姓的报案后,雷厉风行,把这名“恶少”抓起来,依法处理。于成龙不等军营派人来质问,主动出击,带着相关案卷到军营里找“大将军”,详细说明情况,同时要求“大将军”申明军令,不要纵容部下骚扰民间。
当时的情形十分有趣。“恶少”的身份特殊,他被斩首正法以后,十几万军人立即骚动起来,咆哮呐喊,围攻于成龙。而于成龙呢,威武不能屈,义正辞严地向“大将军”说明情况,“词譬理解,神色抗厉”。骚乱的军人看吓不倒于成龙,过了一阵子也就慢慢散开了。陈廷敬的传记文字写得十分生动,好像有一种天崩地裂之感。据常规推测,十几万军人一起骚动的可能性不大,最多就是有“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军人在起哄。
另一件与百姓有关。
清军的情报人员打听到,武昌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私藏兵器,暗地里勾结吴三桂,准备搞“里应外合”的事情。张朝珍接到情报,就准备派兵前去抓捕。这时候,熟悉民间下情的于成龙立即阻止道:“自战争发生以来,武昌、黄州等地的大户人家,都逃到了梁子湖一带避难,家里只留了一部分仆人看守。他们携带兵器,只是自卫防盗,不可能有其他阴谋。如果派兵抓捕,只怕会引起民间的恐慌。”
张朝珍听了,没有立即派兵,而是先让人调查一下,事实果然是于成龙说的那样。于成龙可谓是“料事如神”。富室大户如果真的要暗通吴三桂,肯定会住在城里,伺机举事,怎么可能出城避难?怎么可能只留少数仆人看守门户?
造桥失职
于成龙驻守蒲圻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咸宁和蒲圻修造两座军用桥梁。咸宁桥容易修,很快就完了工。蒲圻桥的工程却有难度,于成龙和属员们商量,征调船只,定于四月二十九日将船只编联成一座浮桥。
当时是洪涝季节,大雨不止,山洪暴发,河流水涨,搭桥十分不易。蒲圻桥一直拖到五月十日方才勉强开工,十一日草草完工。就在这天,传来了咸宁桥被洪水冲垮的消息。于成龙大惊失色,于十二日赶往咸宁,准备重新搭桥。之后发现,不仅刚搭建的浮桥被冲垮,另一座古石桥也被洪水冲垮了。恰在这时,一队清军行至河边,要求渡河。老天爷和勤政的于成龙开了一个大玩笑,延误军机,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
领兵的将军移文湖广巡抚,要求严惩造桥失职的官员。张朝珍责令于成龙如实汇报。心惊胆战的于成龙只能说:“咸宁桥成,洪水冲坏,是实天降灾殃也!”
大洪水连坚固的石桥都能冲塌,何况是仓促搭建、质量难保的浮桥?
张朝珍巡抚一向很器重于成龙,两人可能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于成龙尊称张朝珍为“抚台”“宪台”,张朝珍则亲切地称于成龙为“亲翁”。但是,出了这样的失职大事,军方的文件已经移送过来了,张朝珍不能不如实奏报朝廷,请求惩办“责任人”。朝廷很快就下达了处理文件,将于成龙“革职”。
这是于成龙出仕十几年来第一次受处分,他的心情当然是糟透了。
东山叛乱
在“三藩之乱”影响下,黄州等地蛰伏多年的“蕲黄四十八寨”秘密组织,也在酝酿着揭竿而起,反清复明。
这次起义的核心智囊人物,叫黄金龙。他是河南人氏,另有一说是湖北大冶人氏,懂一些道术,自称得到了上天赐予的天书和宝剑,要辅佐明朝宗,恢复大明的江山社稷。他的这种民间宗教特点,很容易吸引和团结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而起义的领袖人物,名叫刘启祯,字君孚,是麻城东山曹家河人。他是位坚定的“反清复明”人士,其名“启祯”暗含“天启崇祯”之义,字“君孚”也有“不忘故君”之义。他是“蕲黄四十八寨”的秘密领袖之一,在民间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平时期,官府比较倚重他,借助他来办理盗案,于成龙镇守歧亭时,就曾经任用过刘启祯。
黄金龙一直在四处活动,他和刘启祯有共同的政治理想,交往很多,经常住在刘启祯的家里。吴三桂知道黄州一带暗藏有反清复明势力,就派人送来许多“委任状”,鼓动大家起事。这些委任状用清朝的话说,就是“伪札”了。刘启祯等人,在内心里不一定支持吴三桂,但知道这是个大好时机,天下战火四起,清廷手忙脚乱,如果举兵起义,很有可能恢复大明江山。黄金龙和刘启祯四处串联,与“蕲黄四十八寨”及河南、安徽、江西各省的反清复明势力秘密商议,任命将帅,准备聚众数十万,于康熙十三年七月正式起义。在黄州本地,只有木樨河夏鼎安及其族人200余名不肯依附刘启祯。其余的都参与了起义的密谋。
当时,麻城知县屈振奇并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他按照上级命令,严厉追查吴三桂的“伪札”,经常抓捕嫌疑犯。而一些劣绅酷吏,却又借机生事,诬陷攀扯,借着“伪札”的事情公报私仇,这就激化了矛盾。刘启祯养子刘青藜的保户杨楚乔被官府抓捕,屈打成招;徐家堡的周美公等人被官府抓捕,严刑拷打。刘启祯误以为官府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内幕,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于五月十五日,很仓促地在曹家河举兵造反。
本来是接连数省、数十万人同时发难的大型的“反清复明”的起义,现在演变成了“官逼民反”的中小型叛乱,这就是历史的奇诡之处,也是于成龙的命运转机。
定计招抚
刘启祯匆匆起兵后,程镇邦、鲍洪公、陈恢恢、李公茂等几股势力也起兵响应。知县屈振奇并非懦弱无能之辈,他请黄州副总兵王宗臣率军驻扎兴福寺,自己率乡勇驻扎白杲镇,约定日期,准备共同剿匪。刘启祯则更厉害,只派了七名骑兵,晚上偷袭王宗臣的军营,就把王宗臣和屈振奇的兵马逼回了县城。这时候,麻城东山的“蕲黄四十八寨”势力,都纷纷起兵,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
东山叛乱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昌,巡抚张朝珍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如果刘启祯的起义军成了气候,长江中游下游将被隔断,不仅湖北一带两面受敌,河南、安徽、江西乃至江苏等省也都会受到压力,整个战局可能都要发生变化。但这个时候,朝廷大军正在全力进攻湖南的吴三桂叛军,战争打得十分艰苦,很难分出兵力来平息黄州叛乱。
于成龙这时候正在武昌待罪,爱喝酒的他,成天醉醺醺的,给人一副失意酒徒的形象。张朝珍把他召到辕门,商量剿抚大计。于成龙在黄州为官多年,长期驻守麻城歧亭,与刘启祯的关系十分密切,知道“蕲黄四十八寨”的底细。他和张朝珍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不能把黄州叛乱认定为“反清复明”的政治性事件,只按“官逼民反”“赤子弄兵”的普通事件处理,采用“招抚”策略,暂时稳定局势,然后再相机行事,瓦解整个起义。于成龙在黄州威望很高,官绅百姓都十分信服他。张朝珍就决定委派于成龙前往黄州,主持“招抚”大计。于成龙则向张朝珍提出要求,允许他“便宜行事”,打破常规、放开手脚去解决这个复杂问题,张朝珍都答应了。对于成龙来说,这实在是“立功赎罪”“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当时武昌的官员们都信不过于成龙,认为他一介文官,又是个好酒贪杯之人,怎么能办好这样的大事呢?
但张朝珍主意已定,用人不疑,坚决支持于成龙的行动。
劝谕百姓
于成龙于五月二十二日从武昌出发,只带了驻守蒲圻时的几名随从,二十四日到达黄州麻城县白杲镇,此地距刘启祯的山寨只有十里路。他撰写了一篇《初抚东山遣牌》,以父母官的口吻,回忆自己与黄州百姓的鱼水深情,对黄州百姓备加关怀、慰问,对起兵叛乱的事情表示无限的遗憾与责备。他把告示贴到各处,声称自己向巡抚苦苦哀求,阻挡住了大兵征剿,要求百姓们到白杲镇找他来倾诉冤屈,让他来评判是非,早日恢复地方平静。如果百姓们不给他面子,那他就只有回省,请巡抚派兵来剿杀了。
他又撰写《劝畈间归农谕》,大讲副总兵王宗臣的好话,说他也是爱民如子,慈悲心肠,带兵来麻城,主要还是安抚百姓,并非前来剿杀。另外,他又向道台徐惺、巡抚张朝珍两次发文,要求释放被错抓的良民百姓,平息民怨。
后世有很多人都说于成龙此时用的是欺骗手段来骗取老百姓的信任。其实,于成龙此举虽然有智谋的成分,但劝谕老百姓放下刀枪,回乡务农,过太平日子,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是讲“天理良心”的。
黄州麻城一带的士绅百姓,对于成龙是十分崇敬和信任的,也是十分畏惧的,一看于大人来了,都纷纷赶到白杲镇,诉说冤屈,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接受招抚。轰轰烈烈的刘启祯起义,就像一个还没有完全吹起来的大气球,被于成龙轻轻地拔掉了气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