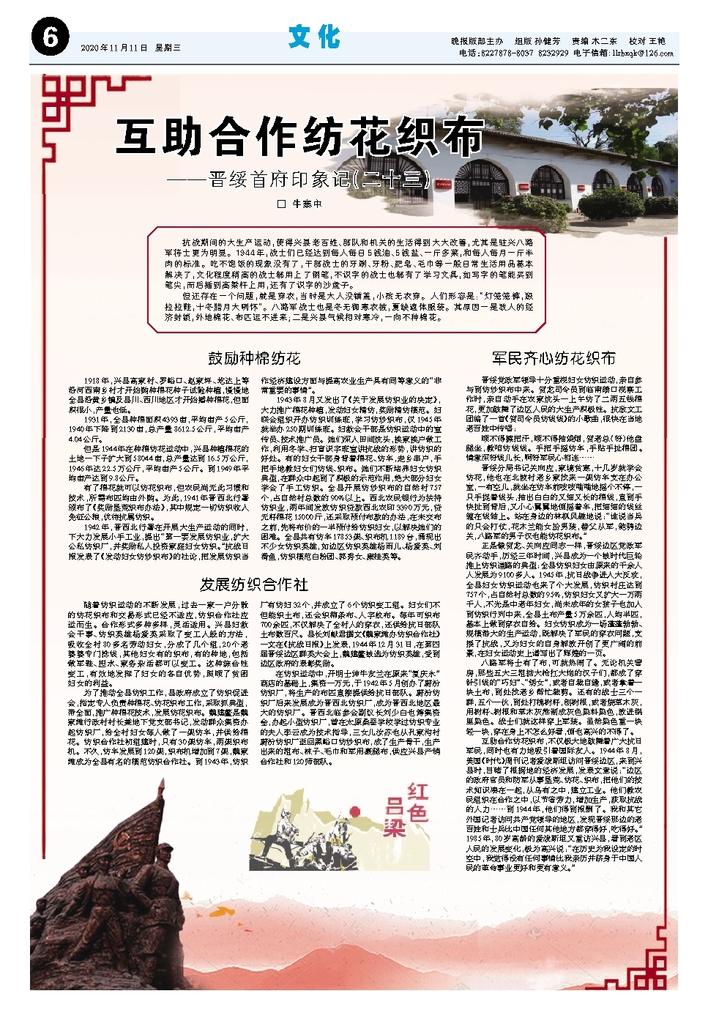□ 牛寨中
抗战期间的大生产运动,使得兴县老百姓、部队和机关的生活得到大大改善,尤其是驻兴八路军将士更为明显。1944年,战士们已经达到每人每日5钱油、5钱盐、一斤多菜,和每人每月一斤半肉的标准。吃不饱饭的现象没有了,干部战士的牙刷、牙粉、肥皂、毛巾等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基本解决了,文化程度稍高的战士都用上了钢笔,不识字的战士也都有了学习文具,如写字的笔能买到笔尖,而后插到高粱杆上用,还有了识字的沙盘子。
但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穿衣,当时是大人没铺盖,小孩无衣穿。人们形容是:“灯笼笼裤,趿拉拉鞋,十冬腊月大咧怀”。八路军战士也是冬无御寒衣被,夏缺遮体服装。其原因一是敌人的经济封锁,外地棉花、布匹运不进来;二是兴县气候相对寒冷,一向不种棉花。
鼓励种棉纺花
1918年,兴县高家村、罗峪口、赵家坪、圪达上等沿河西南乡村才开始购种棉花种子试验种植,慢慢地全县沿黄乡镇及县川、西川地区才开始播种棉花,但面积很小,产量也低。
1931年,全县种棉面积4393亩,平均亩产5公斤,1940年下降到2130亩,总产量8612.5公斤,平均亩产4.04公斤。
但是1944年在种棉纺花运动中,兴县种植棉花的土地一下子扩大到58044亩,总产量达到16.5万公斤,1946年达22.5万公斤,平均亩产5公斤。到1949年平均亩产达到9.8公斤。
有了棉花就可以纺花织布,但农民尚无此习惯和技术,所需布匹均由外购。为此,1941年晋西北行署颁布了《奖励垦荒织布办法》,其中规定一切纺织收入免征公粮,优待抗属纺织。
1942年,晋西北行署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下大力发展小手工业,提出“第一要发展纺织业,扩大公私纺织厂,并奖励私人投资家庭妇女纺织。”抗战日报发表了《发动妇女纺纱织布》的社论,把发展纺织当作经济建设方面与提高农业生产具有同等意义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1943年8月又发出了《关于发展纺织业的决定》,大力推广棉花种植,发动妇女精纺,奖励精纺模范。妇联会组织开办纺织训练班,学习纺纱织布,仅1945年就举办250期训练班。妇救会干部是纺织运动中的宣传员、技术推广员。她们深入田间炕头,挨家挨户做工作,利用冬学、扫盲识字班宣讲抗战的形势,讲纺织的好处。有的妇女干部身背着棉花、纺车,走乡串户,手把手地教妇女们纺线、织布。她们不断培养妇女纺织典型,在群众中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绝大部分妇女学会了手工纺织。全县开展纺纱织布的自然村757个,占自然村总数的90%以上。西北农民银行为扶持纺织业,两年间发放纺织贷款西北农印3390万元,贷无籽棉花15000斤,还采取预付布款的办法,在未交布之前,先将布价的一半预付给纺织妇女,以解决她们的困难。全县共有纺车17853架、织布机1189台,涌现出不少女纺织英雄,如边区纺织英雄杨雨儿、杨爱英、刘滑鱼,纺织模范白粉团、郭秀女、康桂英等。
发展纺织合作社
随着纺织运动的不断发展,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的纺花织布和交易形式已经不适应,纺织合作社应运而生。合作形式多种多样,灵活适用。兴县妇救会干事、纺织英雄杨爱英采取了变工入股的方法,吸收全村80多名劳动妇女,分成了几个组,20个老婆婆专门捻线,其他妇女有的织布,有的种地,包括做军鞋、担水、家务杂活都可以变工。这种综合性变工,有效地发挥了妇女的各自优势,照顾了贫困妇女的利益。
为了推动全县纺织工作,县政府成立了纺织促进会,指定专人负责种棉花、纺花织布工作,采取抓典型,带全面,推广种棉花技术,发展纺花织布。魏建鳌是魏家滩行政村村长兼地下党支部书记,发动群众集资办起纺织厂,给全村妇女每人做了一架纺车,并供给棉花。纺织合作社初组建时,只有30架纺车,两架织布机。不久,纺车发展到120架,织布机增加到7架,魏家滩成为全县有名的模范纺织合作社。到1943年,纺织厂有纺妇32个,并成立了6个纺织变工组。妇女们不但能织土布,还会织柳条布、人字纹布。每年可织布700余匹,不仅解决了全村人的穿衣,还供给抗日部队土布数百尺。县长刘献君撰文《魏家滩办纺织合作社》一文在《抗战日报》上发表,1944年12月31日,在第四届晋绥边区群英大会上,魏建鳌被选为纺织英雄,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
在纺织运动中,开明士绅牛友兰在原来“复庆永”商店的基础上,集资一万元,于1942年5月创办了蔚汾纺织厂,将生产的布匹直接提供给抗日部队。蔚汾纺织厂后来发展成为晋西北纺织厂,成为晋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晋西北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也筹集资金,办起小型纺织厂,曾在太原桑蚕学校学过纺织专业的夫人李云成为技术指导,三女儿汝苏也从孔家沟村蔚汾纺织厂返回黑峪口纺纱织布,成了生产骨干,生产出来的粗布、袜子、毛巾和军用裹腿布,供应兴县产销合作社和120师部队。
军民齐心纺花织布
晋绥党政军领导十分重视妇女纺织运动,亲自参与到纺纱织布中来。贺龙司令员到临南碛口视察工作时,亲自动手在农家炕头一上午纺了二两五钱棉花,更加鼓舞了边区人民的大生产积极性。抗敌文工团编了一首《贺司令员纺线线》的小歌曲,很快在当地老百姓中传唱:
顾不得擦把汗,顾不得抽袋烟,贺老总(呀)他盘腿坐,教咱纺线线。手把手摇纺车,手贴手扯棉团。情意深呀线儿长,啊呀军民心相连……
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家境贫寒,十几岁就学会纺花,他也在北坡村老乡家找来一架纺车支在办公室,一有空儿,就坐在纺车前吱吱嗡嗡地摇个不停,一只手捉着线头,抽出白白的又细又长的棉线,直到手快扯到背后,又小心翼翼地倒摇着车,把细细的线丝缠在线轴上。站在身边的林枫风趣地说:“谁说当兵的只会打仗,花木兰能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边关,八路军的男子汉也能纺花织布。”
正是像贺龙、关向应同志一样,晋绥边区党政军民齐动手,历经三年时间,兴县成为一个被时代巨轮推上纺织道路的典型:全县纺织妇女由原来的千余人人发展为9100多人。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全县妇女纺织运动也来了个大发展,纺织村庄达到757个,占自然村总数的95%,纺织妇女又扩大一万两千人,不光是中老年妇女,尚未成年的女孩子也加入到纺织行列中来,全县土布产量5万余匹,人均半匹,基本上做到穿衣自给。妇女纺织成为一场蓬蓬勃勃、规模浩大的生产运动,既解决了军民的穿衣问题,支援了抗战,又为妇女的自身解放开创了更广阔的前景,在妇女运动史上谱写出了辉煌的一页。
八路军将士有了布,可就热闹了。无论机关营房,那些五大三粗掂大枪扛大炮的汉子们,都成了穿针引线的“巧妇”、“绣女”,或者自裁自缝,或者拿着一块土布,到处找老乡帮忙裁剪。还有的战士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处打槐树籽,刨树根,或者烧草木灰,用树籽、树根和草木灰熬制成灰色染料染色,放进锅里染色。战士们就这样穿上军装。虽然染色重一块轻一块,穿在身上不怎么好看,倒也高兴的不得了。
互助合作纺花织布,不仅极大地鼓舞着广大抗日军民,同时也有力地吸引着国际友人。1944年8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访问晋绥边区,来到兴县时,目睹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发表文章说:“边区的政府官员和防军从事垦荒、纺花、织布,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凑在一起,从乌有之中,建立工业。他们教农民组织在合作之中,以节省劳力,增加生产,获取抗战的人力……到1944年,他们得到报酬了。我和其它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晋绥那边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穿得好,吃得好。”1985年,80岁高龄的爱泼斯坦又重访兴县,看到老区人民的发展变化,极为高兴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