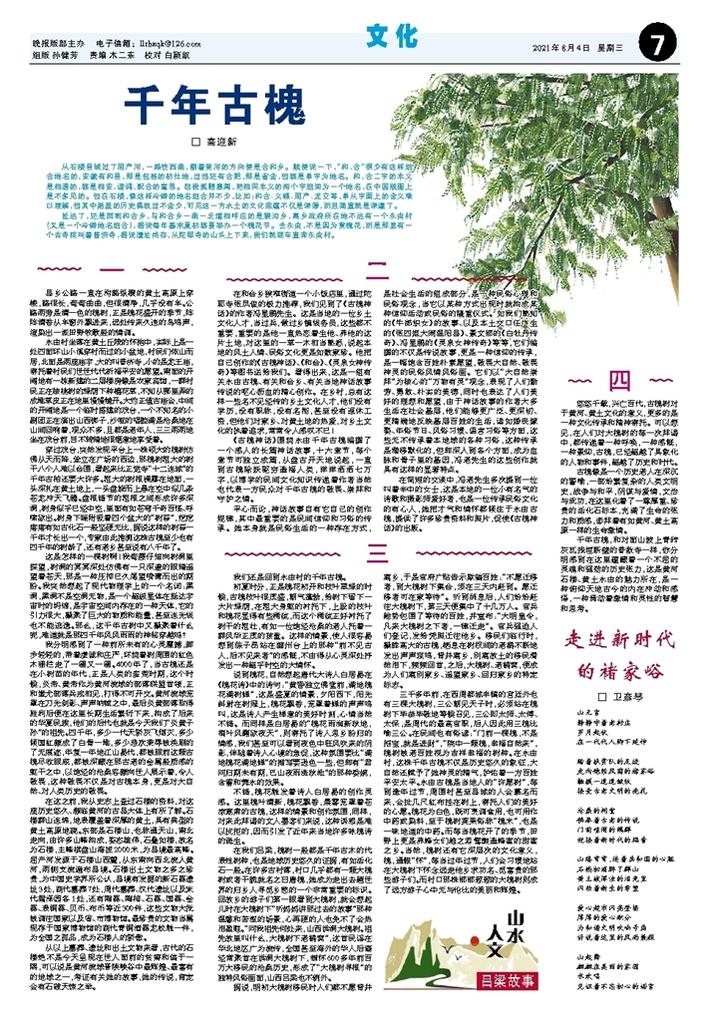从石楼县城过了屈产河,一路往西南,朝着黄河的方向便是合和乡。顺便说一下,“和、合”很少有这样组合地名的,安徽有和县,那是包拯的初仕地,当然还有合肥,那是省会,但都是单字为地名。和、合二字的本义是相通的,都是相安、谐调、配合的意思。恕我孤陋寡闻,把相同本义的两个字组词为一个地名,在中国版图上是不多见的。但在石楼,像这样冷僻的地名组合并不少,比如:和合、义碟、屈产、龙交等,单从字面上的含义难以理解,但其中涵盖的历史典故当不会少,可见这一方水土的文化底蕴不仅是深厚,而且简直就是深邃了。
扯远了,还是回到和合乡,与和合乡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是裴沟乡,离乡政府所在地不远有一个永由村(又是一个冷僻地名组合),据说每年春末夏初都要举办一个槐花节。去永由,不是因为赏槐花,而是那里有一个古寺院叫着普济寺,据说遗址尚存,从陀耶寺的山头上下来,我们就驱车直奔永由村。
一
县乡公路一直在沟豁纵横的黄土高原上穿梭,路很长,弯弯曲曲,但很清净,几乎没有车。公路两旁是清一色的槐树,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阵阵清香从车窗外飘进来,远处传来久违的鸟鸣声,渲染出一派田野牧歌般的情调。
永由村坐落在黄土丘陵的怀抱中,实际上是一处四面环山小溪穿村而过的小盆地,村民们依山而居,北面是两座庙宇,大的叫普济寺,小的是龙王庙,寄托着村民们世世代代祈福平安的愿望。南面的开阔地有一栋新建的二层楼房像是农家宾馆,一群村民正在核桃树的绿荫下种植花草,不知从哪里弄的成堆草皮正在地里慢慢铺开。大约正值古庙会,中间的开阔地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戏台,一个不知名的小剧团正在演出山西梆子,沙哑的唱腔满是沧桑地在山间回响着,观众不多,且都是老年人,三三两两地坐在戏台前,目不转睛地很惬意地享受着。
穿过戏台,突然发现平台上一株硕大的槐树仿佛从天而降,耸立在广场的西边,那槐树粗大的树干八个人难以合围,看起来比正觉寺“十二连城”的千年古柏还要大许多。粗大的树根裸露在地面,一头深扎在黄土地上,一头盘旋而上悬在空中似几条苍龙冲天飞腾。盘根错节的粗根之间形成许多深洞,树身似乎已经中空,里面有如苍穹千奇百怪、呼啸欲出。树身下端附吸着四个盆大的“树苔”,疙疙瘩瘩有如古化石一般坚硬无比,据说这样的树苔一千年才长出一个,专家由此推测这株古槐至少也有四千年的树龄了,还有老乡甚至说有八千年了。
这是怎样的一棵树啊!我弯腰仔细向树洞里探望,树洞的冥冥深处仿佛有一只深邃的眼睛遥望着苍天,那是一种压抑已久渴望喷薄而出的期盼。我突然想起了现代物理学上的一个名词:黑洞,黑洞不是空洞无物,是一个超级星体在抵达宇宙时的坍缩,是宇宙空间内存在的一种天体,它的引力很大,凝聚了巨大的物质和能量,甚至连光线也不能逃逸。那么,这千年古树中又凝聚着什么呢,难道就是那四千年风风雨雨的神秘穿越吗?
我分明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脚步轻轻的,带着虔诚和庄严,环绕着树周围的红色木珊栏走了一圈又一圈。4000年了,当古槐还是在小树苗的年代,正是人类的蛮荒时期,这个时候,炎帝、黄帝作为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首领,正和蚩尤部落兵戎相见,打得不可开交。黄河流域笼罩在刀光剑影、声声呐喊之中,最后炎黄部落取得胜利后便在这里长期生活繁衍下来,构成了后来的华夏民族,他们的后代也就是今天我们“炎黄子孙”的祖先。四千年,多少一代天骄灰飞烟灭,多少倾国红颜成了白骨一堆,多少悲欢荣辱被洗刷的了无痕迹,年复一年地江山易代,都被眼前这颗古槐尽收眼底,都被深藏在那古老的金属般质感的躯干之中,以饱经的沧桑容颜向世人展示着,令人敬畏,这种敬畏不仅是对古槐本身,更是对大自然、对人类历史的敬畏。
在这之前,我从史志上查过石楼的资料,对这座历史悠久、濒临黄河的古县大体上有所了解。石楼群山连绵,地表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具有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东部是石楼山,也称通天山,南北走向,由许多山峰构成,姿态雄伟,石叠如楼,故名为石楼,主峰棋盘山海拔2000米,为县境最高峰。屈产河发源于石楼山西麓,从东南向西北流入黄河,两侧支流遍布县境。石楼出土文物之多之珍贵,为中国史学界所公认,县境有发掘的新石器遗址3处,商代墓葬7处,周代墓葬、汉代遗址以及宋代漏泽园各1处,还有陶器、陶棺、石器、国器、金器、表铜器、贝币、布币等近300件,这些文物大批被调往国家以及省、市博物馆。最珍贵的文物当属现存于国家博物馆的商代青铜酒器龙纹触一件,为全国之孤品,成为石楼人的骄傲。
从以上墓葬、遗址和出土文物来看,古代的石楼绝不是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贫瘠和偏于一隅,可以说是黄河流域晋陕峡谷中最辉煌、最富有的地域之一,考证有关她的故事,她的传说,肯定会有石破天惊之举。
二
在和合乡狭窄街道一个小饭店里,通过陀耶寺张凤俊的极力推荐,我们见到了《古槐神话》的作者冯星鹏先生。这是当地的一位乡土文化人才,当过兵,做过乡镇线务员,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热恋着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相当熟悉,说起本地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更是如数家珍。他把自己创作的《古槐神话》、《和合》、《灵泉女神传奇》等图书送给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一组有关永由古槐、有关和合乡、有关当地神话故事传说的呕心沥血的精心创作。在乡村,总有这样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乡土文化人才,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名衔,甚至没有退休工资,但他们对家乡、对黄土地的热爱,对乡土文化的执着追求,常常令人感叹不已!
《古槐神话》围绕永由千年古槐编撰了一个感人的长篇神话故事,十六章节,每个章节可独立成篇,从盘古开天地说起,一直到古槐除妖驱穷造福人类,洋洋洒洒七万字,以博学的民间文化知识传递着作者当然也代表一方民众对千年古槐的敬畏、崇拜和守护之情。
平心而论,神话故事自有它自己的创作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民间信仰和习俗的传承。她本身就是民俗生活的一种存在方式,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民俗心理和民俗观念,当它以某种方式出现时就构成某种信仰活动或民俗的隆重仪式。如我们熟知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以及本土交口任广生的《张四姐大闹温阳县》、景文郁的《白牡丹传奇》、冯星鹏的《灵泉女神传奇》等等,它们编撰的不仅是传说故事,更是一种信仰的传承,是一幅饱含百姓朴素愿望,敬畏大自然、敬畏神灵的民俗风情风俗画。它们以“大自然崇拜”为核心的“万物有灵”观念,表现了人们勤劳、勇敢、朴实的美德,同时也表达了人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望,由于神话故事的作者大多生活在社会基层,他们能够更广泛、更深切、更精确地反映基层百姓的生活,诸如婚丧嫁娶、年俗节日、风俗习惯、语言习俗等方面,这些无不传承着本地域的各种习俗,这种传承是潜移默化的,但却深入到各个方面,成为血脉和骨子里的基因,冯老先生的这些创作就具有这样的显著特点。
在简短的交谈中,冯老先生多次提到一位叫着辛中的女士,这是本地的一位小有名气的诗歌和摄影师爱好者,也是一位传承民俗文化的有心人,她把才气和情怀都倾注于永由古槐,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和照片,促使《古槐神话》的出版。
三
我们还是回到永由村的千年古槐。
初夏时分,正是槐花初开和枝叶翠绿的时候,古槐枝叶很茂盛,朝气蓬勃,给树下留下一大片绿荫,在粗大身躯的衬托下,上段的枝叶和槐花显得有些稀疏,而这个稀疏正好衬托了树干的粗壮,有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托着一群风华正茂的孩童。这样的情景,使人很容易想到陈子昂站在幽州台上的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慨,不由得从心灵深处抒发出一种超乎时空的大情怀。
说到槐花,自然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槐花诗》中的诗句:“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这是盛夏的情景,夕阳西下,阳光斜射在树冠上,槐花飘香,笼罩着蝉的声声鸣叫,这是诗人产生禅意的美好时刻,心情当然不错。而同样是白居易的“槐花雨润新秋地,桐叶风翻欲夜天”,则寄托了诗人思乡盼归的情感,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夜色中狂风吹来的阴影,伴随着诗人心境的急促,这种氛围要比“满地槐花满地蝉”的描写要逊色一些,但却有“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的那种委婉,含蓄和隽永的效果。
不错,槐花触发着诗人白居易的创作灵感。这里槐叶清新,槐花飘香,晨雾笼罩着苍凉寒肃的古槐,这样的情景和创作氛围,同样,对来此拜谒的文人墨客们来说,这种诱惑是难以抗拒的,因而引发了近年来当地许多咏槐诗的诞生。
在我们吕梁,槐树一般都是千年古木的代表性树种,也是地域历史悠久的证据,有如活化石一般。在许多古村落,村口几乎都有一颗大槐树或者干脆就名之曰唐槐,她成为走出去趟世界的归乡人寻觅乡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回故乡的游子们第一眼看到大槐树,就会想起儿时在大槐树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那种温馨和苦涩的场景,心再硬的人也免不了会热泪盈眶。“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鹤窝”,这首民谣在华北地区广为流传,全国甚至海外的华人后裔经常聚首在洪洞大槐树下,缅怀600多年前百万大移民的沧桑历史,形成了“大槐树寻根”的独特风俗画面,山西吕梁也不例外。
据说,明初大槐树移民时人们都不愿背井离乡,于是官府广贴告示欺骗百姓:“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听到消息后,人们纷纷赶往大槐树下,第三天便集中了十几万人。官兵趁势包围了等待的百姓,并宣布:“大明皇令,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迁往他乡。移民们临行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背井离乡,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之后,大槐树、老鹤窝,便成为人们离别家乡、遥望家乡、回归家乡的特定标志。
三千多年前,在西周都城丰镐的宫廷外也有三棵大槐树,三公朝见天子时,必须站在槐树下毕恭毕敬地等候召见,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是周代的最高官职,后人因此用三槐比喻三公。在民间也有俗谚:“门前一棵槐,不是招宝,就是进财”,“院中一颗槐,幸福自然来”,槐树被老百姓视为吉祥幸福的树种。在永由村,这株千年古槐不仅是历史悠久的象征,大自然还赋予了她神灵的精气,护佑着一方百姓平安太平。永由古槐是当地人的“许愿树”,每到逢年过节,周围村甚至县城的人会慕名而来,会扯几尺红布挂在树上,寄托人们的美好的心愿。槐花为白色,既可烹调食用,也可用作中药或染料,至于槐树荚果俗称“槐米”,也是一味地道的中药。而每当槐花开了的季节,田野上更是养蜂女们趋之若鹜酿造蜂蜜的甜蜜之乡。当然,槐树还有它深层次的文化意义,槐,通假“怀”,每当过年过节,人们会习惯地站在大槐树下怀念远走他乡求功名、觅富贵的那些游子们。而村口那株郁郁葱葱的大槐树则成了远方游子心中无与伦比的美丽和辉煌。
四
悠悠千载,兴亡百代,古槐树对于黄河、黄土文化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可以想见,在人们对大槐树的每一次拜谒中,都传递着一种呼唤,一种感慨,一种景仰,古槐,已经超越了具象化的人物和事件,超越了历史和时代。
古槐像是一个历史老人在深沉的警喻,一部纷繁复杂的人类文明史,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文治与武功,在这里化着了一尊厚重、珍贵的活化石标本,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质感,澎拜着有如黄河、黄土高原一样的生命激情。
千年古槐,和对面山坡上青砖灰瓦残垣断壁的普救寺一样,你分明感到在这里蕴藏着一个不屈的灵魂和强劲的历史张力,这是黄河石楼、黄土永由的魅力所在,是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和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和灵性的智慧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