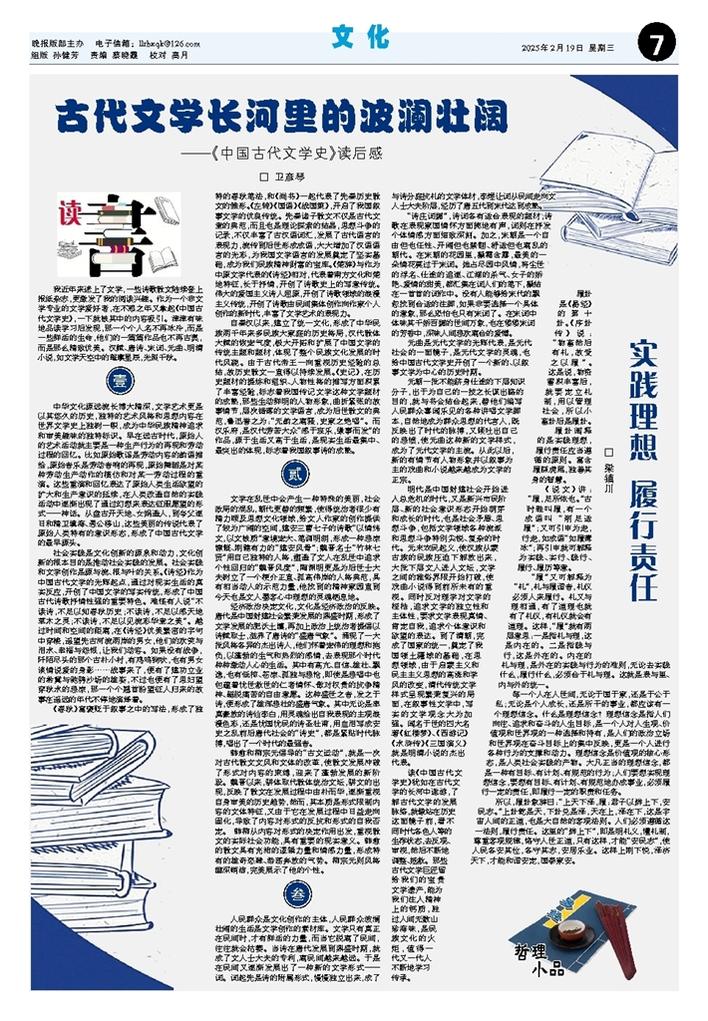□ 卫彦琴
我近年来迷上了文学,一些诗歌散文陆续登上报纸杂志,更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作为一个非文学专业的文学爱好者,在不惑之年又拿起《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下就被其中的内容吸引。津津有味地品读学习后发现,那一个个人名不再冰冷,而是一些鲜活的生命,他们的一篇篇作品也不再古奥,而是那么精致优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如文学天空中的璀璨星辰,光照千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学艺术更是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容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和审美趣味的独特标识。早在远古时代,原始人的艺术活动就主要是一种生产行为的再现和劳动过程的回忆。比如原始歌谣是劳动内容的韵语描绘,原始音乐是劳动音响的再现,原始舞蹈是对某种劳动生产动作的模仿和对某一劳动过程的重演。这些重演和回忆表达了原始人类生活欲望的扩大和生产意识的延续,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出现了通过幻想来表达征服愿望的形式——神话。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夸父逐日和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美丽的传说代表了原始人类特有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早源头。
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实践和文学创作是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光辉起点,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应,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抒情性强的重要特色。难怪有人说“不读诗,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诗经》优美繁密的字句中穿梭,遥望先古河流两岸的男女,他们的欢笑与泪水、幸福与怨恨,让我们动容。如果没有战争,阡陌尽头的那个古朴小村,有鸡鸣狗吠,也有男女谈情说爱的身影……战事来了,便有了建功立业的希冀与驰骋沙场的雄姿,不过也便有了思妇望穿秋水的悲凉,那一个个翘首盼望征人归来的故事在遥远的年代不停地演绎着。
《春秋》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写法,形成了独特的春秋笔法,和《尚书》一起代表了先秦历史散文的雏形。《左转》《国语》《战国策》,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优良传统。先秦诸子散文不仅是古代文章的典范,而且也是理论探索的结晶,思想斗争的记录,不仅丰富了古汉语词汇,发展了古代语言的表现力,流传到后世形成成语,大大增加了汉语语言的光彩,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我们民族精神财富的宝库。《楚辞》与作为中原文学代表的《诗经》相对,代表着南方文化和楚地特征,长于抒情,开创了诗歌史上的写意传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开创了诗歌领域的浪漫主义传统,开创了诗歌由民间集体创作向作家个人创作的新时代,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现力。
自秦汉以来,建立了统一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格局,汉代散体大赋的恢宏气度,极大开拓和扩展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和题材,体现了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时代风貌。由于古代帝王一向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故历史散文一直得以持续发展。《史记》,在历史题材的提炼和组织、人物性格的描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标志着我国传记文学这种文学题材的成熟,那些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紧张的故事情节,层次错落的文学语言,成为后世散文的典范,鲁迅誉之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而汉乐府,是汉代劳苦大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现实生活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标志着我国叙事诗的成熟。
文学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美丽,社会政局的混乱,朝代更替的频繁,使得统治者很少有精力顾及思想文化领域,给文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建安三曹七子的诗歌“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建安风骨”;魏晋名士“竹林七贤”用自己独特的人格,塑造了文人在乱世中追求个性回归的“魏晋风度”,陶渊明更是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一个梗介正直、孤高伟岸的人格典范,具有相当动人的示范力量,他找到的精神家园直到今天也是文人墨客心中理想的灵魂栖息地。
经济政治决定文化,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形成了文学发展的肥沃土壤,再加上政治上统治者提倡以诗赋取士,滋养了唐诗的“盛唐气象”。涌现了一大批风格各异的杰出诗人,他们怀着宏伟的理想和抱负,以蓬勃的生气和热烈的感情,去表现那个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生活。其中有高亢、自信、雄壮、飘逸,也有低抑、苍凉、孤独与悲怆,即使是悲唱中也包蕴着忧世救世的仁者情怀、傲对权贵的抗争精神、超脱痛苦的自由意愿。这种盛世之音,发之于诗,便形成了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其中无论是率真豪放的诗仙李白,用灵魂绘出自我表现的主观浪漫色彩,还是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用血泪写成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的“诗史”,都是紧贴时代脉搏,唱出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是一次对古代散文文风和文体的改革,使散文发展冲破了形式对内容的束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魏晋以来,骈体取代散体统治文坛,骈文的出现,反映了散文在发展过程中由朴而华,逐渐重视自身审美的历史趋势,然而,其本质是形式限制内容的文体特征,又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日益走向固化,导致了内容对形式的反抗和形式的自我否定。 韩柳从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出发,重视散文的实际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韩愈的散文具有充沛的逻辑力量和情感力量,形成特有的雄奇恣肆、浩荡奔放的气势。柳宗元则风格幽深峭洁,完美展示了他的个性。
人民群众是文化创作的主体,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素材库。文学只有真正在民间时,才有鲜活的力量,而当它脱离了民间,往往就会枯萎。当诗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就成了文人士大夫的专利,离民间越来越远。于是在民间又逐渐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词起先是诗的附属形式,慢慢独立出来,成了与诗分庭抗礼的文学体材,李煜让词从民间走向文人士大夫阶层,经历了唐五代到宋代达到成熟。
“诗庄词媚”,诗词各有适合表现的题材,诗歌在表现家国情怀方面掷地有声,词则在抒发个体情感方面细致深刻。加之,宋朝是一个自由但也任性、开阔但也禁锢、舒适但也离乱的朝代。在宋朝的花园里,凝霜含露,最美的一朵情花莫过于宋词。她占尽园中风情,将尘世的浮名、仕途的追逐、江湖的杀气、女子的娇艳、爱情的甜美,都汇集在词人们的笔下,凝结在一首首的词作中。没有人能够给宋代的飘忽找到合适的注脚,如果非要选择一个具体的意象,那么恐怕也只有宋词了。在宋词中体味其千娇百媚的世间万象,也在缕缕宋词的芳香中,深味人间悲欢离合的爱憎。
元曲是元代文学的光辉代表,是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是元代文学的灵魂,也给中国古代文学史开创了一个新的、以叙事文学为中心的历史时期。
元朝一批不能跻身仕途的下层知识分子,出于为自己的一技之长谋出路的目的,就与书会结合起来,替他们编写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讲唱文学脚本,自然地成为群众思想的代言人,既反映出了时代的脉搏,又倾吐出自己的悲愤,使元曲这种新的文学样式,成为了元代文学的主流。从此以后,新的有情节有人物形象并以叙事为主的戏曲和小说越来越成为文学的正宗。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总危机的时代,又是新兴市民阶层、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开始萌芽和成长的时代,也是社会矛盾、思想斗争,包括文学领域各种流派和思想斗争特别尖锐、复杂的时代。元末农民起义,使汉族从蒙古族的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大批下层文人进入文坛,文学之间的雅俗界限开始打破,使戏曲小说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反对理学对文学的桎梏,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求文学表现真情、肯定自我,追求个体意识和欲望的表达。到了清朝,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我国领土疆域的基础,在思想领域,由于启蒙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高涨和学风的改变,清代传统文学样式呈现繁荣复兴的局面,在叙事性文学中,写实的文学观念大为加强。闻名于世的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是明清小说的杰出代表。
读《中国古代文学史》犹如在古代文学的长河中遨游,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就像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看不同时代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去反观、审视,然后不断地调整、拯救。那些古代文学巨匠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学遗产,能为我们注入精神上的钙质,胜过人间无数山珍海味,是民族文化的火炬,值得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学习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