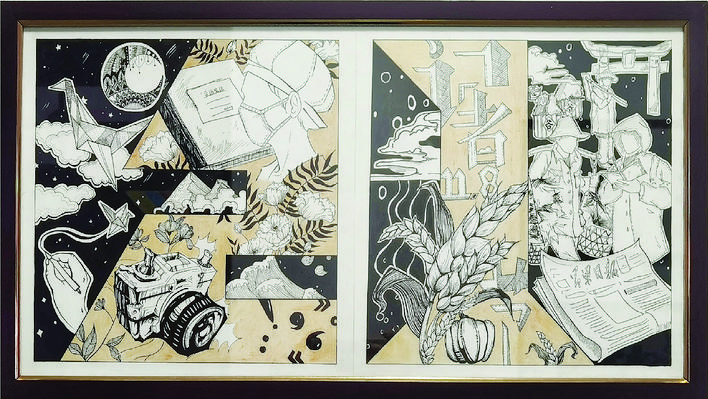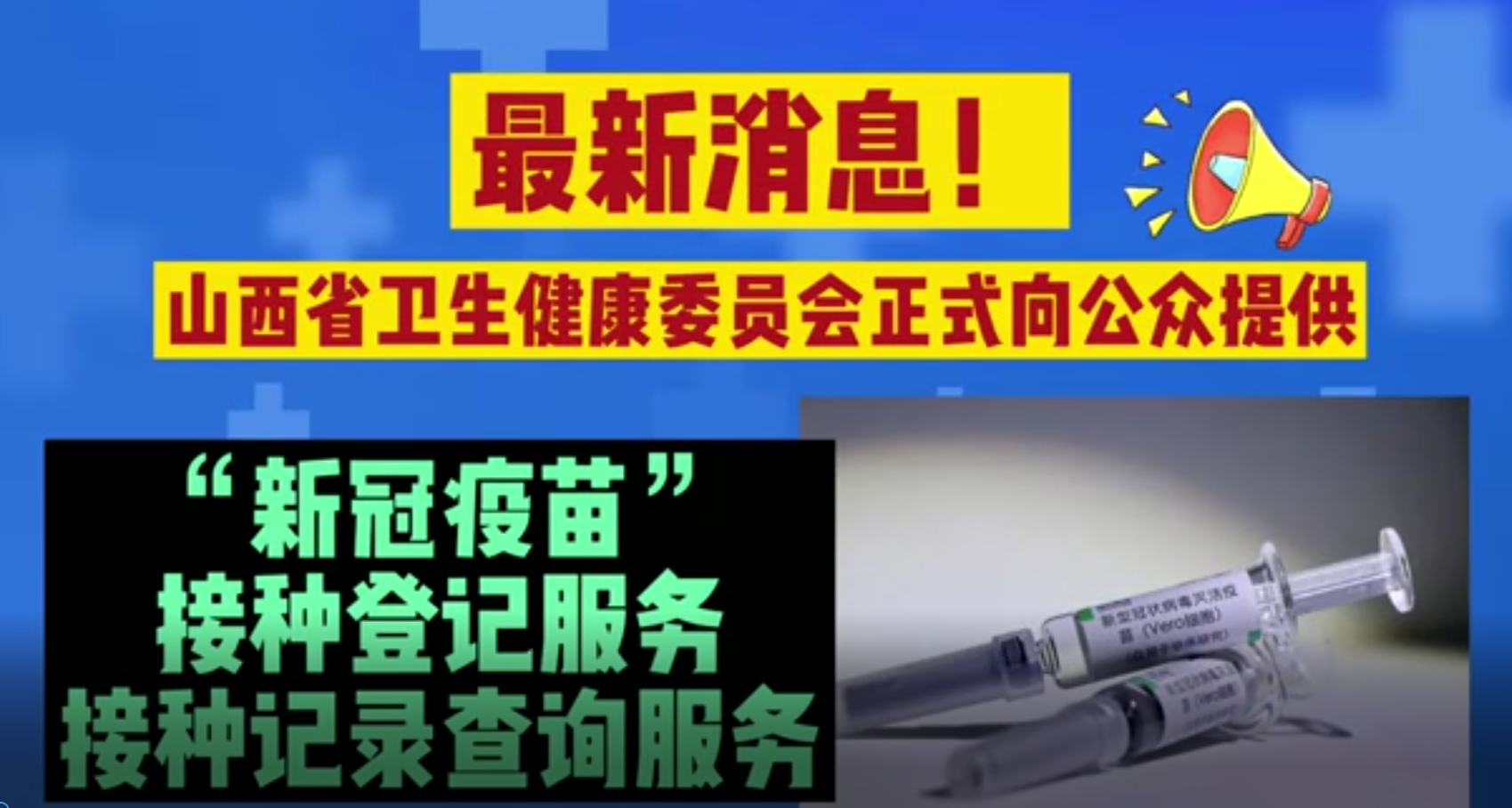空 镜 头
◇评论随笔
□ 李 峰
拍摄很成功的一些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一个非常显著之处,就是准确和恰到好处地运用空镜头。这是考量一部片子艺术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
水墨是国画语言,油画颜料是油画的语言。摄像机拍出的画面,是电视艺术的语言,而画面中的空镜头,那是电视艺术语言中的极品。
正确运用空镜头,在电视艺术中至关重要。
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句诗出自鲁迅先生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与杜甫诗句“城春草木深”有相似的意境。我们常说“大象无形”“大象无声”。那么高大伟岸的大象,怎么能无形、无声呢?“大象无形”是有意化无意,大象化无形,就是不要显刻意,不要过分主张,无形态无框架才能容纳一切形体,最宏伟的形象就是没有形象。“大象无声”也即“大音希声”,是一种艺术和美的最高境界。它是指,最完美的文艺作品都必须进入道的境界,进入自然朴素而没有任何人为痕迹的本真境界。也就是说,大音若无声,大象若无形,直到给人以无音、无形的感觉,从而,至美的形象就到了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这也就是老子“道隐无名”“道可道非常道”和“道法自然”的思路。在我看来,像,是艺术的死敌,是最笨拙的手法,空灵才是最高境界。空,不是没有内容,它不等同于无,而是更宽泛的内含。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无中生有”。而艺术就是无中生有。综观各类艺术,最显著特点,就是传达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传达的方式,不是告诉,不是一字一句道来,而是一种无形的流露,一种体验。具体到一部电视片,在不能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候,就需要使用一些空镜头,这些空镜头的画面、音乐、节奏等,恰好就是那个主题的流露,传达。比如,你要表现一个王朝的更迭、变革,一个家族的衰败、破落,从辉煌荣耀到坍塌破灭的瞬间情绪,你很难找到对应的实体电视语言。这种情况下,用一些夸张后的自然空镜头,比如疾风、暴雨、黑夜等来过渡,就更能有说服力,更有一种情绪的共鸣。在这一点上,我更主张“说出来就不好了”的观点。也就是说“意会比言传”更有味道。
蛙声十里出山泉
《蛙声十里出山泉》是1951年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为文学家老舍画
的一幅水墨画,作品源于老舍先生给齐白石的求画信的影印件。老舍先生的信中其中一句诗便是“蛙声十里出山泉”。白石老人接到老舍先生送来的诗句后,用了三天三夜去思量怎么画才能实现这句诗的意境。现在我们来看这幅作品,整个画面上,留有大块的空白,即天和水的地方不着墨色,留出白纸。从山涧的乱石中泻出一道急流,六只蝌蚪在急流中摇曳着小尾巴顺流而下。我们知道,蝌蚪是青蛙的卵变成的,青蛙在交配前不停地鸣叫,虽然画面上不见一只青蛙,只有六个小蝌蚪,但从画面上的山川、河流、蝌蚪中,仿佛能看到在奔腾的泉水中有青蛙在活动,有“听取蛙声一片”的意境之美。这种表现方法,使画面虚实相生,形神兼备。正由于作者对“时”“空”领域的熟练掌握,才显出一种空灵之美。也有“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大美之境。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画上几只青蛙,那么“蛙声十里”又如何表达呢?“十里”又要用多长的画卷?白石老人发挥了大胆的设想,把蝌蚪与青蛙进行了内在的关联,从而巧妙地构思,表达了主题,成为中国画中的旷世佳品。
再来看一首唐诗《滁州西涧》中的名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唐代大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著名的诗。韦应物天宝末年曾在宫廷担任过玄宗的侍卫官。早年为人任侠,狂放不羁,后来折节读书。滁州,在今安徽省滁县城西,韦应物时任滁州刺史。这首诗是描写诗人不得其用的无奈、忧伤的情怀。诗中表达出诗人独独喜爱涧边生长的幽草,上有黄鹂在树荫深处啼鸣。诗人对此似乎不以为意,自有更重的心思,那就是傍晚下雨潮水涨得更急,郊野的渡口没有行人,一只渡船横泊河里。从这样的画面里,我们能看到诗人在一个幽草丛深、黄鹂鸣叫的景致中,独自站在滁州西涧,即上马河边,望着急雨中的潮起潮落,任一只渡船横泊在河中,风雨飘摇。充分表达出了诗人的忧伤、彷徨和对自己无所作为的伤悲。这样的处境与他的性格、才学,形成了大的反差,但诗人面对这大好的春光,莺歌燕舞的景色,却怀才不遇,无所作为,虽说是一滁州刺史,命运却仿佛那急雨中横泊在河里的一叶小舟,飘摇不定,心神惶惶。
在这首诗里,诗人没有直抒胸意,也没有铺陈仕途的艰难,而是用“幽草”“黄鹂”“春潮”“野渡”,寥寥几笔,勾勒出了一个落魄人的心灵。如果把这首诗用水墨画表现出来,不就是一个很好的空镜头吗。试想我们要用摄像机、编辑机来表现韦应物的这首诗,草是幽草,渡口是野渡,舟是随风摇曳,水是汹涌澎湃的春潮,而黄鹂是古代文人特别喜爱并反复咏唱的一种鸟。最重要的是那个野渡“无人”,真的无人吗?显然不是。而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有一位胸怀大志,但无法施展才华的官员,忧心重重,苦闷郁闷,用“野渡无人舟自横”来表达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只有深刻理解了诗人的创作背景,理解了诗人的心情,我们才能运用镜头和画面,把这种意境表现出来,才能从空镜头的“无人”里,看到“有人”。我们常说“诗画同源”,韦应物的诗,白石老人的画,都为我们在电视片中运用空镜头,做了一个示范,值得我们认真体会,深刻理解。
还须弦外有余音
我国著名的漫画大师、散文家丰子恺先生有两句诗“尝喜小中能
见大,还须弦外有余音”。高度概括了艺术之美。电视片,作为一种艺术的呈现,也必须同其它艺术一样,遵循这种美的规律。电视美学就是要研究如何运用电视艺术手段,认识和反映现实的规律问题。电视语言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表现技巧和手法,而在这其中,空镜头的应用,掌握起来难度是比较大的,需要有相应的美学基础和艺术理论的支撑。语言学中有一个术语,叫“语言构拟”,空镜头就是一种“内心语言构拟”。在一部电视片中,可以写实的东西当然很多,比如对话、事件等,但那些抽象的东西、情绪的东西,又怎么表现呢?我们不妨把“通感”这种审美活动,引入电视片的创作中。
实践证明,在日常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使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各种感觉都产生美感。准确地运用通感,可以“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宋代诗人梅圣俞语)。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有句名言“少即是多”。我说:空不是无。在我们的中国画中有“计白”一说,画面上常常留有一定的素白之纸,这“素白”处,并非无物可画的缺空,而是“计白为墨”,墨出形、白藏象。即所谓“无画处皆成妙镜”(清人笪重光《画筌》)。这在书法作品中,也有一致的“留白”现象,有的笔画看着是断开了,实际上在气势上还连贯着。
再比如,中国的传统戏剧,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虚实相生”,老艺人说过:“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身上”。演员手中摇一支木浆,就表示在江河之上荡舟而行;舞台上放一张桌子两条凳子,就表示一个房间。这就是所谓的“藏境”,用宋人欧阳修《六一诗话》中所引梅圣俞的说法,即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或如清人叶燮所说:“言在此而意在彼”。这就在艺术知觉中形成了一种艺术审美的推理符号系统,从而完成了一次审美的过程。这些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和知识,都为我们年轻的电视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无,这个字是那么高超、那么伟大”“却千万不要把‘无’当成是‘虚无’的无或‘有无’的无”。因此,在创作电视艺术片中,我们也一定要参透“空镜头”的这个“空”字,真正使我们的每个“空镜头”都有无形之“形”和无声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