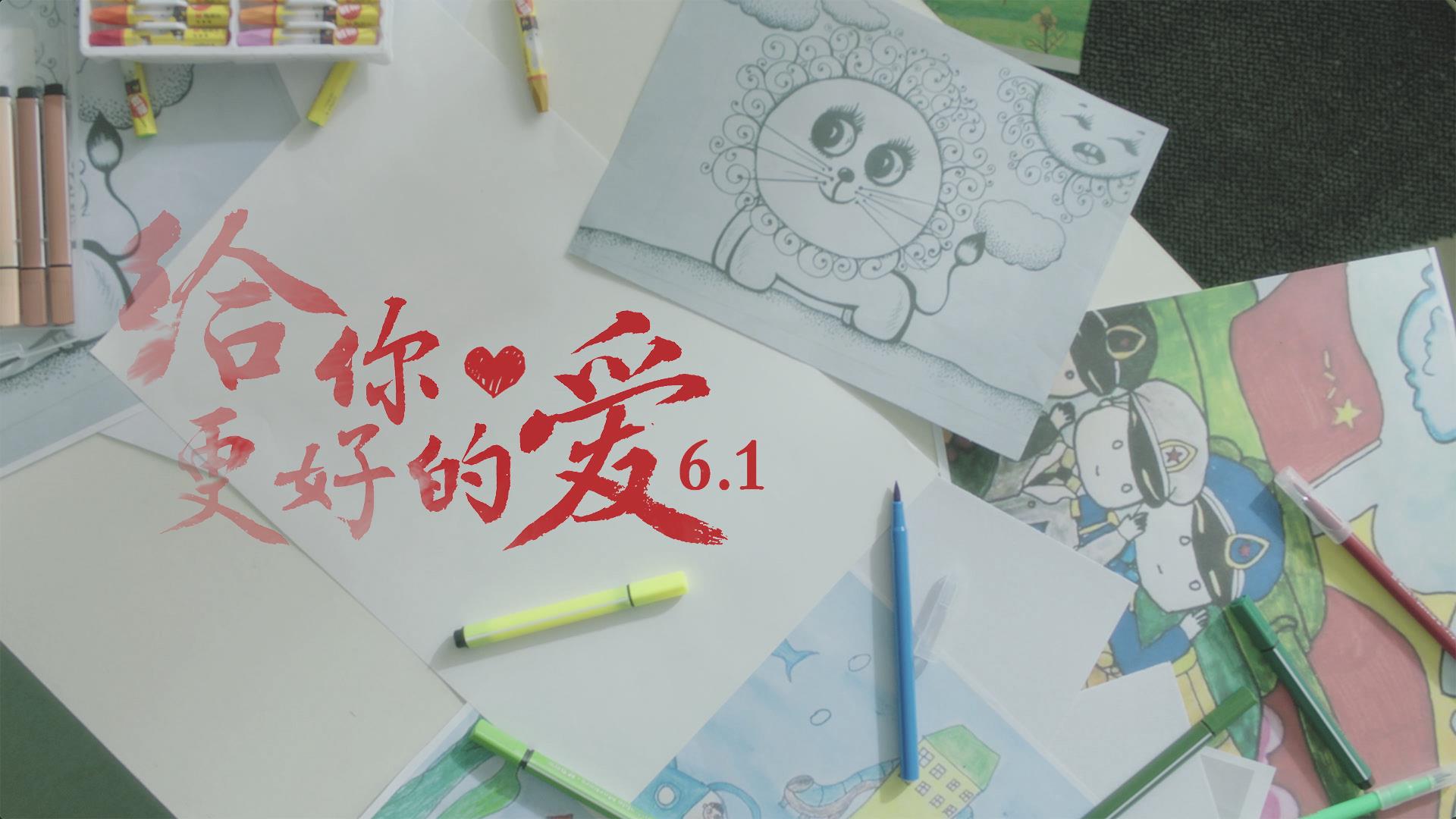变迁
□ 李瑞平
八十年代,我出生在乡下,四十多年的时间,我见证了我们国家一个飞跃式发展的过程,也深刻感受到党的光辉如温煦的阳光一样照耀着整个中华大地。
我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八十年代初,虽然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极度匮乏,许多家庭刚刚解决温饱,吃穿用度都紧紧巴巴。
我无法改变作为四女儿的命运,上小学的时候,穿的衣服都是姐姐们穿旧了的,用的书包,文具都是姐姐们用过的,走在同龄的孩子中间,我经常感到自己很穷酸,衣服不体面,文具不体面,这件事我多次对母亲提过,我要求给我买新书包,要求给我买新文具盒,但我看到母亲很为难,家里拿不出这笔钱,父亲给叔叔娶媳妇花了四百元,我们家买山下的两眼窑洞花了四百多元,这些钱那时候还没有还清,后来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父亲买了一头牛,那头牛的钱还在那儿欠着。
对于家里的经济状况,我并不太懂,觉得我用的钱又没有多少,比起房子和牛来,那几乎是微不足道,我觉得是因为我是四女儿的原因,母亲不看重我。小时候很长的时间,我都对父母充满抱怨。
上了初中后,不知不觉,发现家里的条件渐渐好了,我要订的报刊,要买的文具,只要与母亲提出来,母亲都会满口应承。这时候每到过年,母亲都会去县城扯几块布,自己在缝纫机上给我们缝新衣服,过年不仅有新衣服穿,每到换季,母亲也会买新布给我们做衣服。有一次,我问母亲哪来的钱,母亲说卖粮食卖的,卖猪卖的。那时候对那种细微的变化没有仔细去想,也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但很明显家里的生活渐渐变好了。
但我们家的开支明显地在增加,家里劳力少,孩子们都在上学,那时候我大姐上大学,我二姐上中专,我三姐上高中,所需的学费、生活费虽然国家有很大的补贴,但仍需要家里支援。我看到父母为了能顺利供我们上学,每天起早贪黑的忙,也并没有因为家里负担重,让我们有辍学的打算。
那时候上初中,就在我们乡中学,我们跑校。课余回到家,有许多农活等着我们去做,那时候土地已经承包到户,家家地里有许多活要忙,要给菜园子里的菜浇水,要施肥,要松土,有时候还得帮忙喂牛,喂猪,或者去山上地里锄草。但虽然吕梁山上缺水,那些年,每到秋收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地里没有一块地不丰产,母亲种的小杂粮都装满了家里的水泥箱子,后来有收购粮食的三轮车来村里收购粮食,或者拉来白面和大米,与村里人换余粮。
不知不觉,我们渐渐觉得吃穿用度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母亲赶集的时候,回来给我买了一只发卡,还买了一只崭新的书包,不止我们家,我看到周围的邻居几乎都与我们家差不多,村里人消费的观念不止仅限于生活必需品,一些装饰品也渐渐纳入大家的视野。
后来我上师范,几个姐姐相继毕业,参加工作,父母则依然在土地上劳作,对于生活中发生的变化,我对我们家的变化有切肤的体验,但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们乡下,我们的村庄,都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
在我师范毕业,参加了工作,时光迅捷地流逝,我发现我们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前的河上架起了桥,通村的路都用水泥硬化,村前的河滩地里盖起了几栋楼房,而进出的小汽车畅通无阻。而我遇到的那些爷爷奶奶,虽然他们比我记忆中的样子年迈,但我看到他们精神面貌都很好,心情愉悦。每当站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会感慨一番,说党的政策好,说这个社会好,不缺吃,不缺穿,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才深刻地明白这种生活来自哪里,这种生活由谁缔造。
回到乡下的时候,虽然村庄还是我生活的村庄,但我仿佛感觉它又不是过去的那个村庄,它的面貌焕然一新,村内的巷道都硬化了,再不用下雨天出不了门,即使河里的水上涨,村里人都不用担心过不 了河,各种家电,用水,吃穿,出行,都便捷多了。
我去叔叔家,发现他家安着暖气片,以为是电暖气,叔叔说是水暖,后来仔细一看,发现确实是水暖,这个暖气管道与火膛相连,工艺很简单,但只要火膛里有温度,水管子里的水便会循环到暖气片上,家里马上就暖和了。
乡下有一点比城里好,就是家家都有一个偌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片地,种着葡萄,种着西红柿、黄瓜,种着韭菜,芫荽,什么时候要吃,就到院子里摘一把。乡下的院子里都打了一口井,用水也方便,这光景,确实与我们小时候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都工作后,父母也在城里安家,但会在清明、谷雨等一些节令回一趟乡下,把院子里的葡萄秧从土里刨出来,用铁丝架起来,然后在院子里种上一些蔬菜苗子,等到暑假回乡下避暑的时候,院子里是一片青翠茂盛的景象。
周末,我喜欢随父母一起回乡下看看,有时候会带孩子在暑假里待几天,我经常会带他们去山上,让他们从小感受劳动的辛苦,收获的快乐,并把过去那种艰苦的生活讲给孩子听,我们是真切感受到党的光辉的一代人,也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了解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了解我们党的英明领导,和带领全中国人民所走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