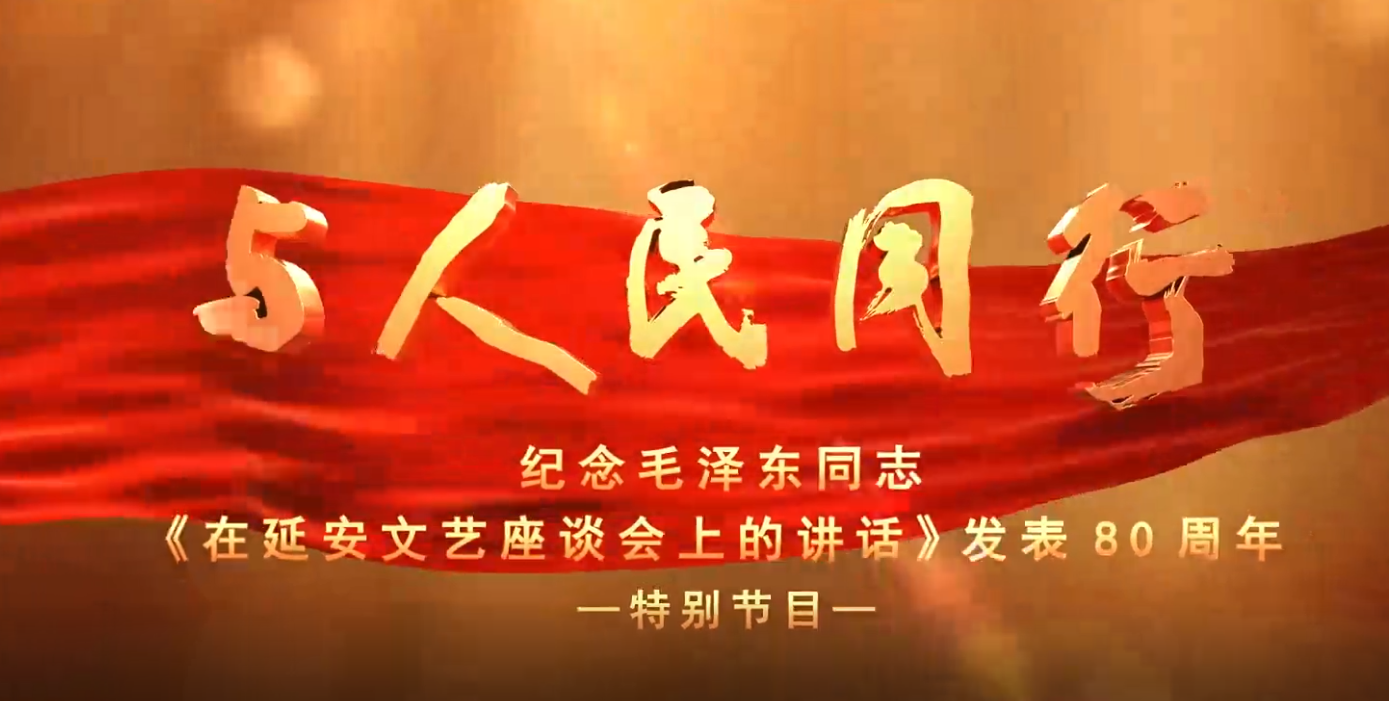滨水狂欢
□ 白军君
闲翻《河防一览》《水经注》,期望能从中找到破译《诗经》中流水阻隔情爱的解释。结果一无所获。思路跑偏了。科学从来解释不了文学,更解释不了文化。
情爱是洪水猛兽,原始时代先民们强烈旺盛的生命热力势如爆发的火山。
汹涌澎湃的爱水必然冲破自然界的河流阻隔和早期人类学文化层面的“河流”的禁锢,去完成人本意义上的男欢女爱,这是人类繁衍的本能,更是人性中最为丰饶和柔嫩的部分。作为最早的文学,《诗经》怎么可以缺席呢?怎么可以不在场呢?
不会的。
于是,“风”来了。再高的山峰挡不住“风”,再宽再深的河流也挡不住“风”。“风”吹来了人间的欢声笑语。
对坝坝的圪梁梁上哪是一个谁?
那就是我要命的二啦妹妹。
没有谁能够阻挡人间“要命”的情爱。有谁敢说这首撕心裂肺的民歌不是《诗经》中《匏有苦叶》的余响和尾音?
自由、真诚的诨言诨语从来都是出自民间,它不作伪、不故作高深 、不假装庄严,它更不会使用“美声唱歌”,于是,“风”自然而然地来了。
葫芦有叶叶味苦,
济水深深也能渡。
水深连衣渡过去,
水浅提衣淌过河。
济河水满白茫茫,
雌野鸡叫声咯咯,
济河虽深不湿轴,
野鸡鸣叫为求偶。
大雁鸣叫声谐和,
东方天明日初升。
你若真心来娶我,
趁冰未化先过河。
多么自然的“通俗唱法”。就《诗经》中的“风”而言,它一定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歌谣,“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风”和文人诗的最大区别就是:不修饰。它想甚唱甚,即景抒情、即事为喻。“济盈不濡轨”——赶紧渡过来吧,河水不深,还没有淹了车轴呢。别怕,水真的不深,你赶紧过来吧。多么家常的语言。古人的示爱就是这么直接,不绕弯儿。喜悦中充满焦躁,憨直而情真。这种热切的爱是原始的,它完全用不着含蓄,也完全用不着深沉。一切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如春天的种子,只要条件适宜,秧苗一定会破土而出。
爱情从来就不好写,主要是很容易写不好。可我要说,在《匏有苦叶》里头,爱情的书写太成功了,他拧巴着写,是凰求凤。它描写的是人类纯情初露、至诚可爱的稀世珍品。
初恋,大多发生在水边。也许水的欢快、清澈、自然在先民们心中和他们的恋情有着惊人的相似?
三月的流水被称作为桃花水,也叫春水。王羲之在流水淙淙的春水边顺手写道: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暮春就是农历三月,“暮春之初”,加上“修禊事也”,那只有上巳节。在永和九年的上巳节,王羲之等一干文人雅士硬是把原本消灾祈福的活动演变为一场名垂千古的盛大的诗文联谊会。我推测,王羲之他们一定也干了别的什么事儿,只是那一纸《兰亭序》名头太过响亮,盖过了别的事情。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是杜甫老先生笔下描写三月初三日的纪实诗句。从古人更多的文字中,我们知道,上巳节是一个从会稽到长安,从东晋到大唐,从杨贵妃到山野村姑,全民嗨皮的重要节日,是古代男女狂欢的日子。这一天的活动项目大致是这样安排的:水边春游。看看花草。洗个野澡。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各自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寻找自己顺眼的异性。遇到看上的人,直接表达,经典路数是:
我摘朵木瓜送给你,只是为了挑逗你,我不要你的琼琚。我不是想要报答你,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
有的妹子死缠烂打,软磨硬泡,她主动邀请一个男孩一起去水边玩,男孩直接拒绝了她。这是两人的对话,我抄录如下:
女:观乎?
士:既且。
《溱洧》中对这个场面的描写非常经典,从文字中,几乎可以看出两人的声口和各自的表情。
“去看水吧?”
“我去过了,不去了。”
妹子没有放弃,她再次邀请:
“且往观乎!”——去过就陪我再去一次嘛。
我敢断定,原文中应该还有对话,被孔圣人删掉了。这句话是这样的:
女:傻哥哥,你真的以为只是去看水啊?
士:那……走吧……
两个陌生的男女就这样完成了第一次约会,他们玩得尽情尽兴,分手时不知谁送给谁芍药——“伊其将虐,赠之以芍药”。
春水涣涣,游人如织,“有女如云”“如荼”,上巳节情爱狂欢的集会“殷其盈矣”,这是多么盛大的场景啊!
古往今来,写人类情爱的文字汗牛充栋,能把两性的狂欢写出酣畅淋漓,纯朴自由,文字中洋溢着清新气息的能有几人?
《诗经》就是《诗经》,孔老夫子没有看走眼。《诗经》是描写人类情爱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