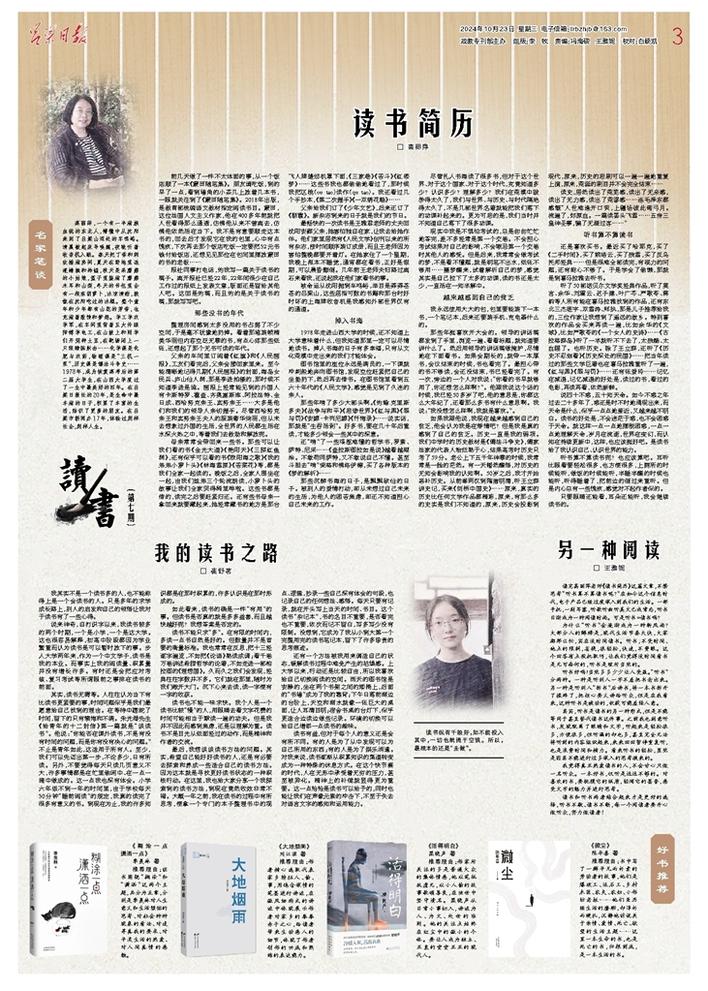前几天做了一件不太体面的事,从一个饭店顺了一本《蒙田随笔集》。朋友请吃饭,到的早了一点,看到墙角的小茶几上放着几本书,一眼就关注到了《蒙田随笔集》。2018年出版,是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目。蒙田,这位法国人文主义作家,他在400多年前就把人世看得那么通透,仿佛他从来不曾离去,仿佛他依然活在当下。我不是有意要顺走这本书的,回去后才发现它在我的包里,心中有点愧疚,下次再去那个饭店吃饭一定要把32元书钱付给饭店,还想见见那位在包间里摆放蒙田的书的老板……
报社同事打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读书的稿子。离开报社已经22年,22年间很少在自己工作过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版面还是留给其他人吧。这回是约稿,而且约的是关于读书的稿,那就写写吧。
那些没书的年代
整理房间感到太多没用的书占据了不少空间,于是毫不犹豫地扔掉。看着那堆装帧精美华丽但内容空泛无聊的书,有点心疼那些纸张,还想起了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
父亲的车间里订阅着《红旗》和《人民画报》,工友们看完后,父亲会搂回家里来。至今能清晰地记得几期《人民画报》的封面,海岛女民兵、庐山仙人洞,那是李进拍摄的,那时候不知道李进是谁。画报上经常能见到的外国人有卡斯特罗、霍查、齐奥塞斯库、阿拉法特、金日成、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大多是他们和我们的领导人亲切握手。尽管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夫人的服装奢华绚丽,但从未去想象过外国的生活,全世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救助和解放呢。
母亲常常会带回来一些书。那些可以让我们看的书《金光大道》《艳阳天》《三探红鱼洞》,还有似乎可以看的书《欧阳海之歌》《我的弟弟小萝卜头》《林海雪原》《苦菜花》等,都是我们全家一起读的。晚饭之后,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由我们姐弟三个轮流朗读,小萝卜头的故事让我们全家哭得稀里哗啦。这些书都是借的,读完之后要赶紧归还。还有些书母亲一拿回来就要藏起来,她经常藏书的地方是那台飞人牌缝纫机罩下面,《三家巷》《苦斗》《红楼梦》……这些书我也都偷偷地看过了,那时候我把区桃(ou tao)读作(qu tao)。我还看过几个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
父亲给我们订了《少年文艺》,后来还订了《朝霞》。新杂志到来的日子就是我们的节日。
最畅快的一次读书是王雅君老师的丈夫回沈阳安葬父亲,她害怕独自在家,让我去给她作伴。他们家里居然有《人民文学》创刊以来的所有杂志,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而且王老师因为害怕整晚都要开着灯。在她家住了一个星期,我晚上根本不睡觉,通宵都在看书,正好是假期,可以晨昏颠倒。几年前王老师夫妇路过离石来看我,还说起我在他们家看书的事。
被命运从沈阳抛到车鸣峪,举目是莽莽苍苍的吕梁山,这些屈指可数的书籍和那台时好时坏的上海牌收音机是我感知外部世界仅有的通道。
掉入书海
1978年走进山西大学的时候,还不知道上大学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那里一定可以尽情地读书。掉入书海的日子有多幸福,只有从文化荒漠中走出来的我们才能体会。
图书馆里的座位永远是满员的,一下课就冲刺般地奔向图书馆,发现空位赶紧把自己的坐垫扔下,然后再去借书。在图书馆里看到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学》,感觉是见到了久违的亲人。
那些年啃了多少大部头啊。《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红与黑》《罪与罚》《安娜·卡列尼娜》《忏悔录》……说实话,那就是“生吞活剥”。好多书,要在几十年后重读,才能多少领会一些其中的深意。
还“啃”了一些艰涩难懂的哲学书,罗素、萨特、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越看越糊涂。不敢苟同萨特,又不敢说自己不懂。甚至斗胆去“啃”荣格和佛洛伊德,买了各种版本的《梦的解析》……
那些沉醉书海的日子,是飘飘欲仙的日子。被别人的爱情打动,却从未想过自己未来的生活,为他人的困苦焦虑,却还不知道担心自己未来的工作。
尽管扎入书海读了很多书,但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时代,究竟知道多少?认识多少?理解多少?我们在荒漠中跋涉得太久了,我们与世界、与历史、与时代隔绝得太久了,不是几部世界名著就能把我们落下的功课补起来的。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落下了很多功课。
现实中我是不惧怕考试的,总是匆匆忙忙地答完,差不多经常是第一个交卷。不会担心考试结果对自己的影响,不会顾忌第一个交卷时其他人的感受。但是后来,我常常会做考试的梦,不是看不懂题,就是钢笔不出水,纸张不够用……噩梦醒来,试着解析自己的梦,感觉其实是自己拉下了太多的功课,读的书还是太少,一直活在一知半解中。
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贫乏
我永远使用大大的包,包里要能装下一本书,一个笔记本,后来还要装手机、充电器什么的。
那些年挺喜欢开大会的。领导的讲话稿都发到了手里,浏览一遍、看看标题,就知道要讲什么了。然后用领导的讲话稿做掩护,尽情地在下面看书。如果会期长的,就带一本厚书,会议结束的时候,书也看完了。最担心带的书不够读,会还没结束,书已经看完了。有一次,旁边的一个人对我说:“你看的书早就够用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已经50多岁了吧,他的意思是,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看那么多书有什么意思啊。我说:“我没想怎么样啊,我就是喜欢。”。
如果我跟他说,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贫乏,他会认为我是在矫情吧?但是我是真的感到了自己的贫乏。历史一直是我的弱项。我们中学时的历史教材是《儒法斗争史》,儒家法家的代表人物烂熟于心,结果高考时历史只考了59分。老公上下五千年神聊的时候,我常常是一脸的茫然。有一天幡然醒悟,对历史的无知会影响我的认知啊。50岁之后,我才开始恶补历史。从前秦两汉到隋唐明清,听王立群讲史记,买来《剑桥中国史》……原来,真实的历史比任何文学作品都精彩,原来,有那么多的史实是我们不知道的,原来,历史会投影到现代,原来,历史的悲剧可以一遍一遍地重复上演,原来,荒诞的剧目并不会完全结束……
读史,居然读出了荒芜感,读出了无奈感,读出了无力感,读出了荒谬感……连毛泽东都感慨“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听书算不算读书
还是喜欢买书。最近买了哈耶克,买了《二手时间》,买了熊培云,买了残雪,买了反乌托邦经典……但是很难全部读完,有视力的问题,还有耐心不够了。于是学会了偷懒,那就是到喜马拉雅去听书。
听了50部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作品,听了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叶广芩、严歌苓、蒋韵等人所有能在喜马拉雅找到的作品,还有东北三杰班宇、双雪涛、郑执,那是儿子推荐给我的,三位作家让我想到了遥远的故乡。特别喜欢的作品会买来再读一遍,比如余华的《文城》,比如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古拉格群岛》听了一半就听不下去了,太残酷、太血腥了。也听历史。除了王立群,还听了《历史不忍细看》《历史深处的民国》……把当年读过的那些文学巨著也在喜马拉雅重听了一遍,《红与黑》《罪与罚》……还有张爱玲……记忆在减退,记忆减退的好处是,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再读再看,依然新鲜。
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如今不惑之年过去二十多年了,惑还是时不时地涌现出来,而天命是什么,似乎一点点地接近,又越来越不明白。读书的好处是,不会迷茫于惑,也不会困惑于天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摆脱困惑,一点一点地理解天命,岁月在流逝,世界在变幻,而认知在持续更新中,这样,也应该挺好吧。是读书给了我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能力。
听书算不算读书呢?也应该算吧。耳听比眼看要轻松很多,也方便很多,上厕所的时候能听,做饭的时候能听,半睡半醒的时候也能听,听得睡着了,把前边的倒过来重听。但是内心总有一些愧疚,感觉对不起作者似的。
只要眼睛还能看,耳朵还能听,我会继续读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