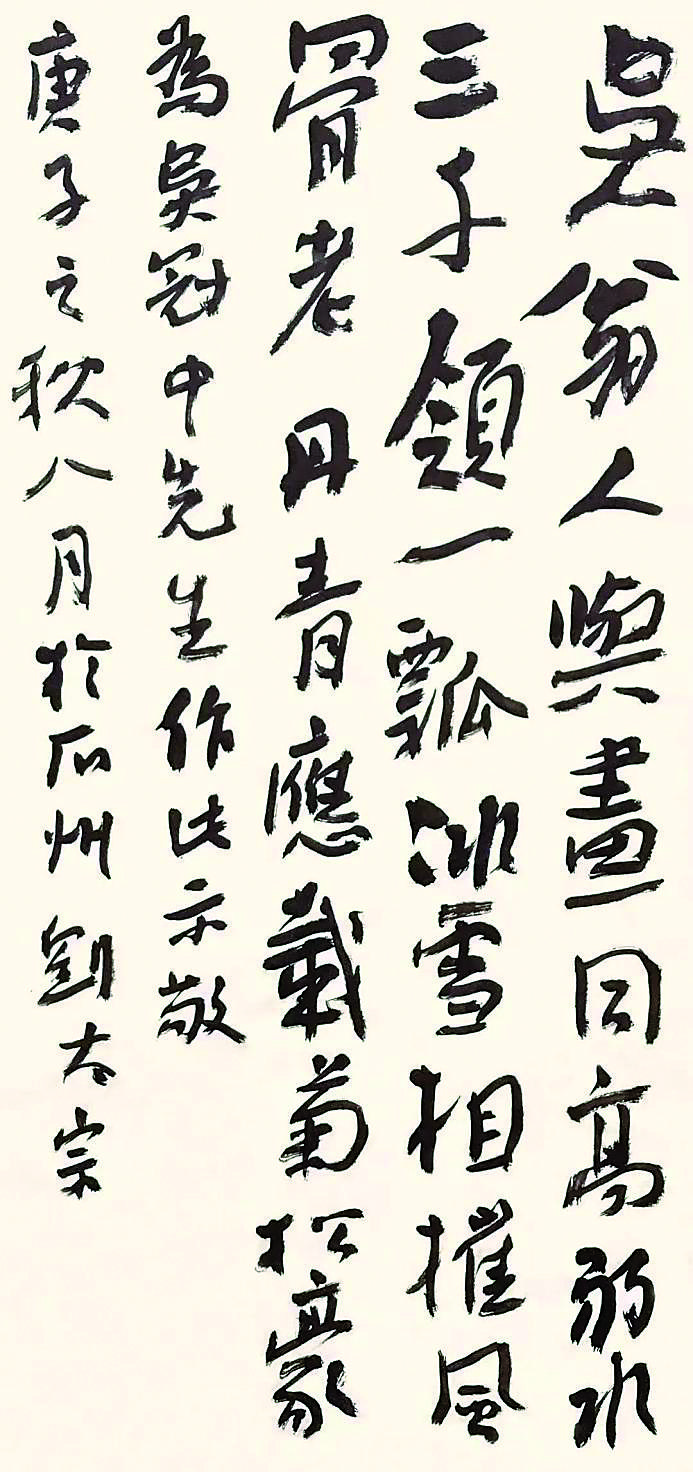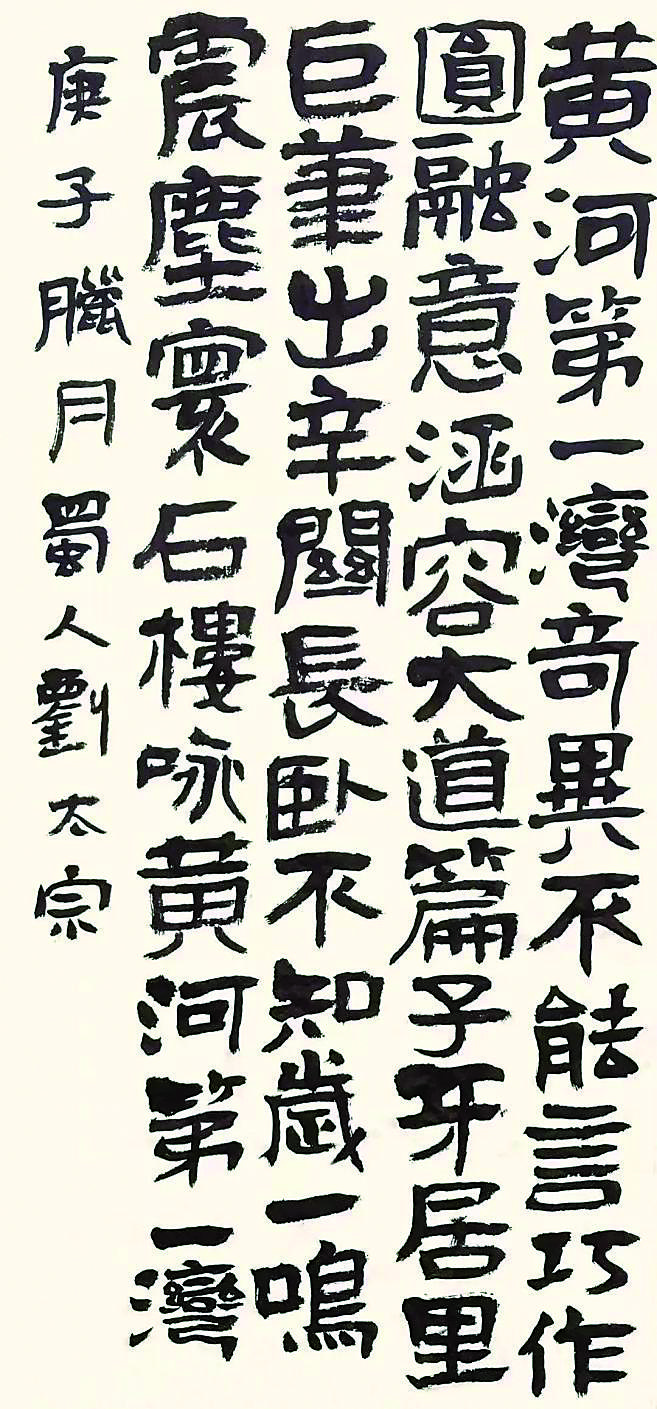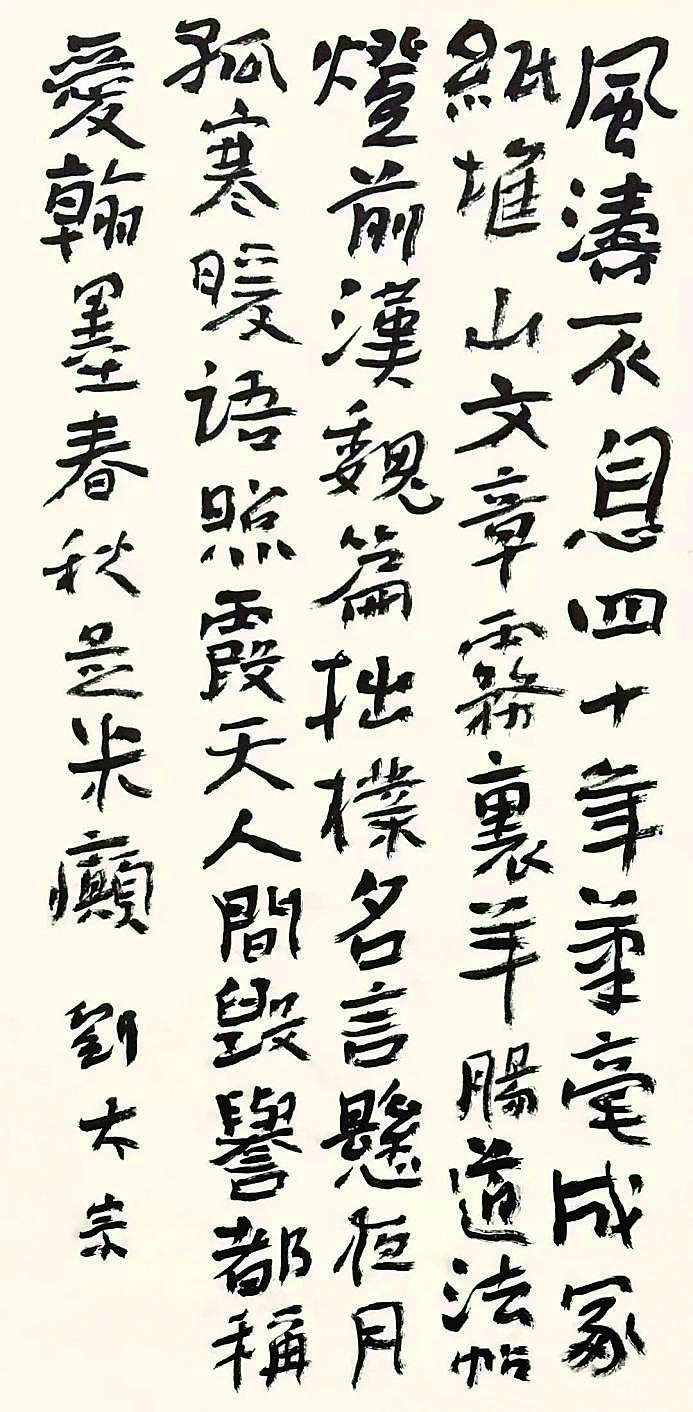韩玉涛先生将唐人孙过庭所著书谱文中的两句话视作中国艺术的艺术方法。这两句话是:“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翻遍古今书论,孙氏之语,鹤立鸡群了。也突显了韩玉涛先生的慧眼。
情动形言的依托是取会风骚之意,是中国艺术源头的诗经楚辞。情动者,诗意也。形言者,墨迹之语也。这是中国书道的前提。不曾濡染于中国文学的诗心,何以言书道!在中国文学的骨子里,丰满着中国文化的林林总总。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儒释道的认知、中国不同时代的文化成就及其代表人物,乃至信仰、道德等等,都是文学的反映对象。杨雄的书为心画,一个心字,包容着无数的中国文化内容,没有这些文化内容的积淀,作为书法艺术作品的迹化,杨雄说的书,(墨迹)何以和心相对?何以如易之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书法艺术就那么一根线,让它负载着书者如此巨量的文心,难道不值得深省吗?
孙氏第二句话,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阳舒阴惨,道之谓也。本乎天地之心,是孙过庭看到了书法艺术的最高审美,是向中国大道的本源回归。王僧虔说,“书之道神采为上”。何谓神,不可知不可为为神。张怀公式称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物类之表,杳冥之间,纯然是体不能够及、语不能到的形而上思维。孙过庭在这里,确立了书道的否定意义:非物。更是确立了书道的肯定意义:归回天地之心,回归于道。作为自觉的书法艺术,从汉代算起,已历两千余年。其魅力,历久弥新。其玄妙,众说纷纭。而到了孙氏此语,我以为一个明确的答案已经成立。他的另一句话:“同自然之妙有”,佐证了回归于道这个命题。自然者,生命之谓也。一切物质世界,都依附于道而存在。自然即宇宙。宇宙显现着无处不在的道。正是如此,“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汉字,是因道而生。汉字的点画及其组合,因六书而成,天地人均在其中。中华民族伟大的语言符号——汉字,同时也是思想符号、情感符号、历史符号、生命形态符号,是一点也不夸张的。统而言之,它就是一个个概念化了的宇宙符号。汉字作为书法艺术的表现对象,其实质是以宇宙符号为表现对象。汉字若没有这个特征,就无法带入书者的情动形言。汉字本身先于艺术而存在的观念形态,使书者主观的个体的人文情怀与天文情怀,由心迹转化为墨迹,成为可能。
所谓宇宙符号,是以宇宙现象为依据的矛盾体。方圆、斜正、上下、左右、高低、疏密、横竖、长短、大小等等矛盾现象。加之,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的独立固化特征,必然使书者的心灵动态介入于这种矛盾现象之中。从而构成主观情感与矛盾体的变通与融合。由是,书法艺术的全过程,是情动形言的主观色彩和宇宙符号的客观矛盾体的互动与交融。是两种观念的协作。
苏东坡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 。诗是语言,语言表达内心的贫乏,当溢而为书,为线的运动时,其节奏、旋律与组合却把心灵运动的每个细节都摄入其中,成为心灵的图像,使书者有超越于诗的满足。韩玉涛先生称,书法艺术是一种诗化,或者就是这种情形吧。
行文至此,关于玄妙的书法艺术,我以十个字作为结语:以人文为念,以天文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