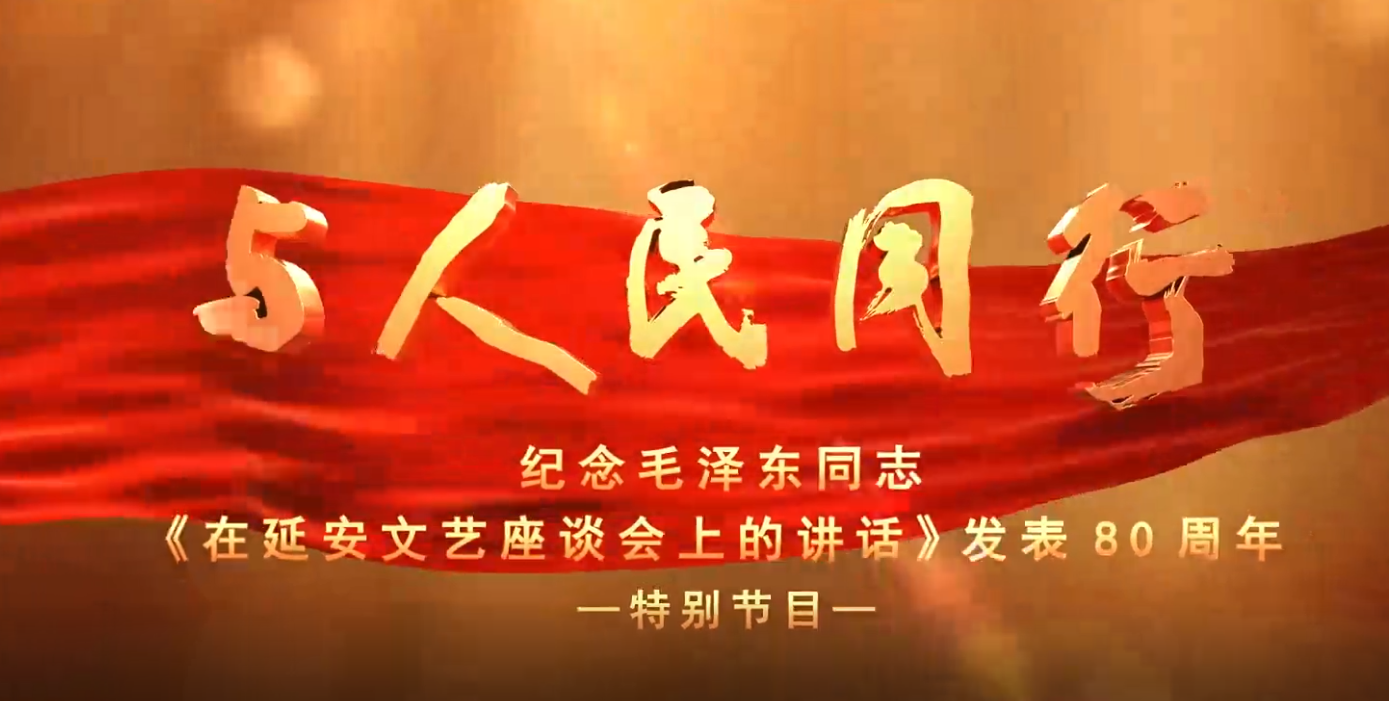◇名家
诗学思语(下)
□ 李 峰
“建筑美”
关于新诗的建筑美,是个伪概念。
新诗是有它特有的美学空间的,也有它特定的美学指向。比如,诗歌的音乐美。因为中国诗歌从第一部《诗经》产生以来,就都与音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都是可以歌唱的。诗歌最早应该是起源于劳动号子。人们劳动累了,用一些简单的词语,组成劳动号子,这些劳动号子多次反复重组重复,形成了固定的旋律。每次劳动累了,便吟唱一番。至今,我们在干家务或劳动时,仍有哼小调的习惯。有时,记不住词了 ,但调子很熟,便把记住的词,挪前攘后。词不对了,但旋律没变。还有在一些文艺节目中,有的人老歌新唱。从古至今的那些歌词,多数可以被看作是诗歌。这是说音乐与诗歌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对的。
但也有人提出新诗也要讲究建筑美。这就有些牵强了。新诗本来就是从旧体诗的樊篱中解脱出来的,就是为了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一次彻底的解放。怎么又要给它制定一个建筑美的标准呢?这无异于又给新诗戴起了一副镣铐。古时候的律诗、绝句,每行每节是几个字就是几个字,平仄押韵是一点都不能不对仗的。当然,这些古典诗歌,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都有流传千年的好诗好句,写成文字放在那里,有一种整齐、统一的建筑美感。但不能不指出也有一种审美疲劳,我指的不只是诗词外观上的形式,更多的时候,由于这种形式的桎梏,也会影响到诗意的纵深。因为它在表达诗情诗性时,僵死的形式,制约了诗人的创造力。因此,难免有同质化或一些牵强附会的东西流露出来。甚至,在很多诗人的诗歌里,看不到诗人的影子,感受不到诗人的灵魂与独特感受。
有人说:不是要向古典诗歌学习吗?这话讲的没错。中国新诗不仅受西方诗歌的影响,而且,在吸收西方诗歌表现手法的同时,仍需要大量地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吸收营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使然,比如《诗经》中的风、雅、颂,比如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比如国人在意境创造中的独特构思,等等。这是我们要坚持向古典诗词学习的东西,但绝不是说新诗也要弯回老路去。也有人提出,新诗也要讲究平仄押韵。这个观点,我坚决不赞成。一切形式都要为内容服务,而不是为了追求形式,让鲜活的语言僵死。当然,诗歌的朗朗上口,没错。但这绝不是新诗好诗的标准。可以在一些朗诵诗中提倡。如前所说的建筑美,事实上,在建筑美学中,中国的审美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西方的十四行抒情诗,是又一码事。
比喻
赋、比、兴,自古以来就是诗歌表现方式的三种重要手段。其中的比,当然就是指比喻。新诗写作自然也离不开比喻。比如,把月亮比作思念,把饮酒比作消愁,把黑夜比作生活的艰难,把阳光比作幸福,等等。四十多年的习诗写诗生涯中,可以说,每首诗都离不开比喻。一开始写时,依葫芦画瓢,大多是沿袭古诗或别人诗里常用的比喻方法,来把意象人格化、形象化,使之具有生命的活力和个性。后来,又从诗歌语言陌生化的角度,和意象解构的层面,在意象表达时,进一步深入到意象的内核,寻找更个性更独特的比喻对象。这主要靠生活的经验和灵感。有时候,还需要站在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使诗歌的比喻更恰当更深刻,更有创意。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至今,仍有许多诗人,包括著名诗人,仍在自己的诗歌里运用这样的比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我认为,诗歌写到能左右逢源,炉火纯青的阶段,怎么写它都是诗。那种比喻是深深地隐藏在每个词和每个句子里,渗透在诗意中了。而不是简单地用“仿佛”、“好像”“如同”“象极了”来僵硬地表达。我写诗,特别是用比喻时,尽量避免用那些直观的比喻,力争寻找诗意的内核。然后,恰到好处地赋予通感、联想。当然,也不是不能用直接的比喻。这只是个老练与不老练的问题。
是不是诗,语言说了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题材、任何素材,都可以写成诗。关键是看怎么写。这里面除了构思、寻找切入点、挖掘诗意、呈现诗眼、把握架构外,我看诗歌的语言,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是不是这个意思。但至少在我的理解中,肯定也包括了这层含义。我们经常说,诗的语言。说明只有用诗的语言,才能写出诗,写出来的分行文字,才能算诗。有人一说到诗的叙事,便把诗写成了分行的散文,写成了打油诗、顺口溜。有人一说到写抒情诗,便只会用“啊”,然后,声嘶力竭地喊,完全失去了诗的美感。有人一说到写朗诵诗,便通篇都是一大段一大段的排比句,一串一串的形容词。这些写出来的东西,都不是诗。初学写诗的人,都有这种激情澎湃的创作经历,而且,也为这些振臂高呼的分行文字,沾沾自喜,兴奋不已。到后来,就感到诗歌越来越没写的了,诗的语言也越来越缺少了。而且,自己再不停地用那些形容词、比喻写诗时,也有一种羞愧的感觉。可以说到了“黔驴技穷”、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就有很多人退出写诗的行列,或者说,这也是很多喜欢文学的人,不敢“触诗”的原因。试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写出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所谓散文。因为,这种文体门槛本身就很低。写的好不好,你不能说它不是散文。但你试着写一首短诗,或一句,那是非常难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一辈子坚持写诗,对诗歌语言深钻细研,对诗学潜心探索,渐渐地就入了写诗的正行。在诗歌语言的研学中,对诗歌“写什么”“怎么写”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最后完成了诗歌“兴之所至”到“心之所至”的转换,写出了很多真正的诗、好诗。
标题
关于诗的标题。每首诗的标题就是这首诗的名字,起的好不好非常重要。毋庸置疑,一首诗的标题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就是说它是对这首诗的高度概括。但诗的标题不同于散文。比如,散文写游记,可以写成“某某地游记”,诗歌不能这么写。诗的标题要写出悟的东西、写出诗人对某种大自然,深刻的理解;诗的标题,可以在整首诗中体现,也可以不体现。主要是看整首诗是不是准确地表达了标题要表现的内容。某种程度上,我更主张,诗的标题不在整首诗中一字不差地体现出来。好像说出来的东西,总是没有神秘感或寡淡的味道。诗的标题,最好是留给读者体会出来,才更有境界;诗的标题,可长可短,没有规定。北岛的《生活》,标题就两个字,内容才一个字,也是好诗。很多诗人,包括一些重要的诗人,不少的诗作标题,大多用两个字。我想,这也算是高度概括了;无题诗不是没有标题,也不是起不了标题,是把标题隐在整首诗作当中了。诗人认为,如果起了标题,反而是画蛇添足。就像无字碑一样,留给人们更多想象的空间。现在就有人专门写这种无题诗。不过,我觉得这样写下去,有点勉强,也没有必要。偶尔写几首无题诗,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不要刻意搞,有做秀的嫌疑。
状态
写诗的状态很多。有的人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或酝酿后,才动笔。甚至还有人为创作一首诗,要查阅很多相关资料或背景素材。有的人是偶有灵感,便提笔赋诗。每个诗人的写作状态都不尽相同。多数情况下,我写诗的状态有两种:一种是偶有触动,便开始下笔。大多时候,是连标题也未想好,只是觉得这个触动,应该用诗表现出来。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把这个触动预想到的结局,改变了。就是说,是在语言的牵引下,为它找到了更美妙的一个出路。如果在状态当中,那些词语就很鲜活地往出蹦。过后,连我也很吃惊。当然,写诗与作文不同,不能提前命题,确立主题思想。这种诗,写出来也没多少诗的味道。我不写;另一种是,先有一个诗意的结局,然后把整首诗倒着写。就是把诗逆向写,诗的结尾确定后,从大脑中开始发动想象,勾连经验,收罗相关意象。看上去,有点铺陈和佐证的意思。事实上,在写诗实践中,想到这个结尾时,脑海中已经翻腾过很多意象,就剩梳理和准确生动地表述了。那种像论文一样,经过缜密构思,然后,付诸文字的诗。我觉得,过于逻辑,过于理性,也许也有写的好的,我没写过。诗歌的发生很奇特,造就了诗人的写作状态不尽相同。只要写出来的是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