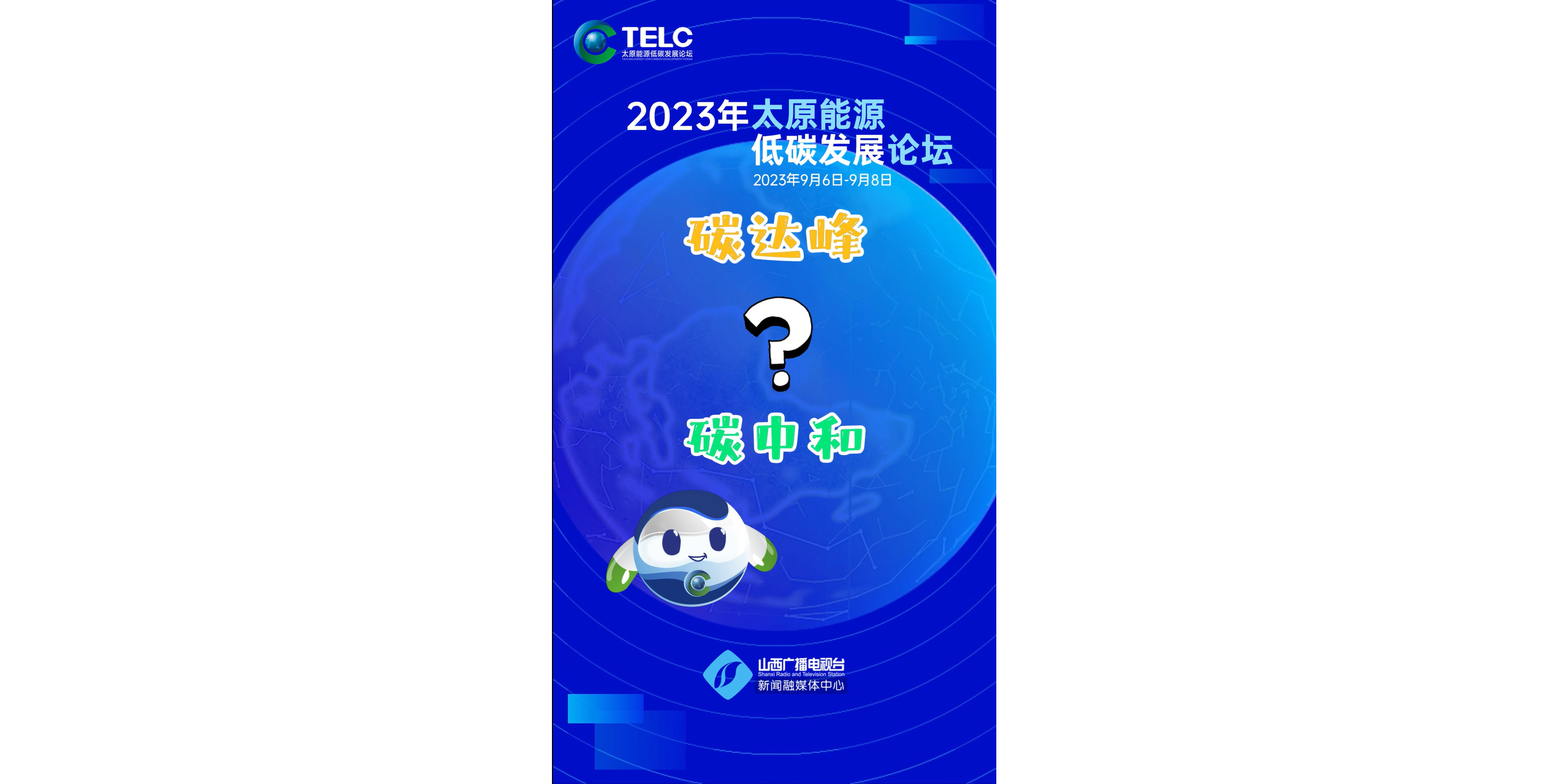拜谒西戎文学纪念馆
□ 马明高

一
其实,很早就有了去蒲县拜谒西戎文学纪念馆的想法了。前几年,我写过一本名为《文人厚土》的书。这是一部写吕梁山与“山药蛋派”文学五主将的书。吕梁山,既是一片英雄的土地,也是一片文学的沃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主要作家与吕梁山有着天然而亲切的联系。我的这本书写的就是,马烽、西戎、孙谦、李束为、胡正,从四面八方来到晋绥革命根据地,相聚吕梁山,参军入党,吕梁剧社生活,发表处女作,延安鲁艺学习,参加群英会,报社生活,还乡曲,参加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吕梁的挂职生活。他们把青春与浪漫都奉献给了这块土地。他们在战斗与工作之余,拿起笔,向与他们遥遥相望的太行山区那位赵树理大哥学习,用农民的语言来描写晋西北的战斗生活与农村生活,创作出了一大批农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学作品。吕梁山成了中国“山药蛋派”文学的摇篮与肥沃厚土。这部纪实的非虚构作品,2020年3月由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通过写这部书,更加深了我对西戎先生的敬仰之情。前些日子,当供职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的作家李景平先生,邀请我参加去蒲县采风的“美丽中国,生态山西”活动时,我非常高兴。我心里想,这下可终于能去蒲县拜谒西戎文学纪念馆了。
其实,和马烽、孙谦一样,西戎也是出生在古老壮观、连绵不断的吕梁山下的。只不过,他是出生在吕梁山脉的西南山脚下。我们去拜谒先生的时候,是在一个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的夏日,远远的望见,在一片翠绿之中,静静地卧着一个村庄,四野无声,有些年老的村民从村里走了出来。这就是西戎先生出生的蒲县化乐镇西坡村。现在西坡村划归黑龙关镇管辖。纪念馆就在先生的故居,是在一棵粗壮高大的老槐树下的一座农家小院。老槐树枝叶茂密墨绿,郁郁葱葱,长得极旺盛。对面的高大院墙壁上,是他和马烽合作的名著《吕梁英雄传》主要场景的浮雕。拐弯,走几步,从一个古朴雅致的小院门进去,就是西戎的故居。
故居坐西向南。一进院门,就能看到对面墙下先生高高的人物塑像。先生表情庄重大气,微微仰头,充满深情的望着从远道而来的我们。院子不是很大,西面现存砖窑3孔,石接土窑洞1孔,是先生小说插图作品展和书法作品展。东面是一间大展馆,为先生生平事迹展。该馆是先生艰苦奋斗、波澜壮阔一生的展示,收藏有很多反映先生革命、工作、创作和生活的珍贵照片和文物。
二
一进展馆,面前就耸立着先生坐着与我们促膝谈心的巨幅画像,旁边写着“西戎生平事迹展”几个大字,左下方是先生自己手书的一首打油诗:“吾本山里娃,竟然成作家。文坛山药蛋,也算一枝花。”书法质朴清秀,内容谦虚低调,极像先生的文字风格与为人处世精神。
先生也没有想到,他会从一个“山里娃”成为一位全国甚至全世界也著名的作家。先生小时候家里还算比较殷实,有平坡地36亩,喂着一头牛、一头驴和二十几只羊。家里有七口人。父亲叫席安行,文盲。母亲叫刘福姐,也是文盲。他们生有五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小,是个“老生子”。因为生在壬戌闺年,满周后,父亲牵上毛驴专程到化乐镇南庙,请能说书会算命占卜的张先生起了一个奶名,喜闺。他的大名席诚正,是堂兄席道正给他起的。西戎是参军以后自己取得笔名。先生从小爱读书,爱看木偶戏和皮影戏。7岁到化乐镇读初小。11岁时考取了蒲县第一高小。当时蒲县无中学。两年后,本想到平阳府报考省立第六中学继续升造。哥哥从微薄的薪水里挤出3元大洋给他做盘缠,他和另外县城里有钱人家的4个同学一行5人,前往平阳府参加考试。三天后,学校出了榜,他被录取了。他高兴得用剩下的一元五角,花一角二分破例给自己吃了一碗肉丝炒面,还和同学们一起进“小沧浪”澡堂洗了澡,理了发,上街给父亲买了包兰州板烟,给母亲置了块黑头帕,给三姐的小女儿买了件小汗衫,高高兴兴回到村里。家里的人们和邻居们都很高兴,向他祝贺。但万万没有想到家里请来的放羊小工,引着牛驴到沟里饮水,让突发其来的山洪把人和牲口冲了个一干二净。倾刻间家里就变得一穷二白。他自己变成了放羊娃。1938年春天,日本人把西坡村烧杀掠抢,成为一片废墟。他和姐姐在地里劳动,忽然又听到了枪炮声。他想自己死也不能当亡国奴,扔下工具,拔腿就往西边的县城跑。跑到县城,找到牺盟会他认识的一个秘书傅东岱。当场唱了一首《松花江上》,因为有文艺特长,同意报名参加了蒲县牺盟会下面的工作团。就这样,他参加了革命,和马烽、孙谦、束为、胡正走到了一起。
整个展馆的顶棚,是一大页《吕梁英雄传》第一回的复印版的放大。一张偌大的洁白的长方形纸上,印着一行又一行黑色的文字。字迹清晰,排列整齐,十分壮观,令人立刻肃然起敬,庄严正穆。
这让我想起了他和马烽在晋绥边区兴县北坡村创作《吕梁英雄传》的艰难岁月。1944年秋天,他和马烽、束为参加完在神木马镇盘塘村的晋西北第四次规模盛大的群英会后,就又回到晋绥大众报社工作。他和马烽决定把群英会上好多民兵英雄的事迹写成章回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当时生活艰苦、工作紧张。白天,他们要跟农民在田间劳动,召开各种会议,征兵,征粮,宣讲减租减息政策。晚上,才能编辑报纸的稿子,写报纸等着连载的章回小说。这样就养成了吸烟提神的习惯。当时,又没有好烟,只能拿稿纸条和生烟叶自己用手卷个前粗后细的“自制烟”。有一次,《抗战日报》的郁文同志来到他们报社,说宣传部的张稼夫部长给了我一盒战缴的“顺风烟”,他说大家辛苦了,犒劳各位,可是中途碰见熟人,已经打劫了多一半,现在只剩下三支,报社4名记者,分两支,剩下一支,只能委屈分给三位编辑伙抽了。一支烟,三个人怎么伙抽呢?西戎在散文《吸烟忆趣》中写道,三人认真讨论,西戎主张把烟掰成三截,各吸一截,公平合理。马烽认为那样要留三个烟蒂,太浪费,不如把烟量好尺寸,画出记号,分成三份,一人吸完另一人接着吸,各吸各的一份,又不浪费。束为和西戎也觉得这样好。马烽用米尺量好距离,画出记号,说西戎年龄小,先吸,他二吸,束为年龄最大,最后轮他。无异议。西戎点着烟,猛吸一口,满嘴芬芳,接着又猛吸一口。马烽当即惊呼,过线了,快拿过来!“说时迟,那时快,趁机我又猛吸了一口”,才顺手把烟交给了马烽。马烽“高擎着香烟,并不马上吸”,而是“拉过一条板凳,正襟危坐”,“慢吸细品,顺手还端过一个搪瓷缸,呷一口水,方把憋在嘴里的烟气送下喉咙。李束为瞅急了,笑道:‘真叫酸劲儿不小!’”一下把马烽逗乐了,喉咙里一岔气,水喷出来,溅了一桌子,把嘴上的烟也洇灭了。纸皮开裂,烟丝散乩。束为忙把散落的烟丝收拢,装进自制的枣木烟斗里,美美的吸着,说好烟,好烟。“马烽一面收拾着喷在稿纸上的水珠,一面带点嫉妒地说:‘今天好活了束为!’”《吕梁英雄传》在报纸上连载后,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1946年,吕梁教育出版社要出版单行本,这是何等的重大的事情!他俩决定趁机好好修改一番。在1946年2月22日西戎写给马烽的一张留言条上,先是写了关于如何再好好修改书的六条意见,又写了两条“又及”:“明天再走,可能坐汽车,但不肯定。再,我走时,因为来不及缝,穿上了束为的裤衩。束为回来,不急需,就等我回来还他,假使急需,就请你给他钱,买一条裤衩的布好了。”我想,他们“五战友”也真是够哥们儿了,竟然好的在现实生活中同穿一条裤衩了。
三
展馆里,有一张他和马烽20世纪50年代在汾阳贾家庄采访村民的照片,我驻足观看着,久久不愿离开。
先生对汾阳县和贾家庄村是有着很深厚的感情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离开老家十几年了,他们“五战友”都想回去看看。1948年冬季,西戎在第二次谈恋爱失败之后,“装着一肚子气,一怒之下,便请假返乡探亲去了”。先生在散文《我是山里娃》中写道,他和胡正结伴南行,从兴县出发,下山后,想先到汾阳城逗留几天,然后再到胡正的老家灵石,他回再蒲县。他们“早就听说汾阳是出美女的地方,他们想了解一下在这里找对象难不难”。他们通过汾阳军政招待站,在城里逛了几天,结果发现,“此地的妇女,水色很好,穿戴也入时,就是适龄女子在汾阳城未解放前,多已嫁给阎锡山的军官当了太太,剩下的年轻女子,有的还在上学,有的对八路军怀有成见,认为嫁给八路军不能享福,要吃苦受穷”。找对象无望,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他们在戏园子里看了几夜晋剧名角马玉楼的戏,就沿着兵站的公路到了灵石。在胡正家住了一夜,他归心似箭,第二天就回到了蒲县西坡村。在父亲的授意下,两位姐夫四处奔走,给他找对象。正好曾和堂兄在县城教过书的李先生有一女儿,叫李英,20岁。两人正好合适,而且不收一文彩礼。由在临汾的堂兄堂嫂张罗,把父亲和李先生都请到堂兄家里,“大家坐在一张桌上,共同吃了一顿酒饭,就算完成了一生的终身大事”。1953年,西戎从四川成都调到北京,他要求回山西“安家落户”。他先到汾阳县挂职县委副书记,派往贾家庄初级社蹲点体验生活。与从北京中国作协青年部任副部长请假回到山西的马烽,到汾阳唐兴庄采访了民兵英雄蒋三儿的故事,决定再合作一部反映吕梁山下平川民兵抗敌斗争的小说。当时在北京电影局工作的孙谦给他俩出主意,最好写成电影剧本。他俩就合写成电影剧本《扑不灭的火焰》,送给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审阅。后又修改好,陈荒煤推荐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汾阳县拍摄,在全国公开放映后,很受全国人民欢迎。我在展馆里,还看到了1956年油印的《扑不灭的火焰》“电影镜头纪录本”。
在展柜里,俯身望着好几本发黄的《宋老大进城》《姑娘的秘密》版本,以及50年代的《人民文学》《火花》杂志,我浮想联翩,不由想起先生和马烽在汾阳一起挂职县委书记,在贾家庄村当蹲点干部的艰苦生活。当时,他们住在村里的龙王庙里,也就是农业社办公的小四合院。西戎在散文《下乡生活漫忆》中写道:他住的是当时一间堆放农具的小库房,“这里经常开干部会,党、团员会,每天黑夜都挤满了人。烟味、汗味,有时呛得人透不上气,想把窗户打开,社里的养猪圈正在窗外,一股股酸臭味随风飘进房里,比房里的烟味、汗味还要令人难么忍受。老社长贾焕星见我揉搓着鼻子,就笑着打趣说:‘席书记,你住的这地方不懒,天天都能上追肥,你将来写咱农业社,可不要落了这一段,也让将来住上洋楼的后辈儿孙知道咱们是怎样创业的!’是的,农村的生活条件,是比不上大城市,但是不下决心住在心里,又怎么能写出真实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来呢!”先生说得多么实在而恳切啊!先生就是在这里接连创作了《宋老大进城》《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等6个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火花》发表,与马烽、孙谦、束为、胡正,迎来了“山药蛋派”文学的第二个辉煌时期。
四
在西面的“西戎书法作品展厅”里,我看见了一幅先生书录赵树理赠盲人赵高升师徒的一首诗,“不受权门白眼睛,朱弦鼓简独天真。香灯伴我朝连夕,残话留人去复停。”我想起了1978年改革开放初,先生第三次攀登文学高峰,创作的《春牛妈》《赵庄闹水》《难忘的一幕》《耿老模》《叔伯兄弟》等优秀作品。特别是在小说《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走向新岗位之前》里,通过对世俗环境和人情世态的描写,对社会上那些干部不正之风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心理剖析,深刻反映出作家对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与现实生活中人们趋炎附势复杂心态的焦虑、难过和担心,表达出了对国家前途与人民命运的深切关心。先生用一生的辛勤劳动和心血智慧,践行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文学追求。他说:“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要忠于人民,要忠于现实,要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揭示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写出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文学作品。现在,我们看来,这个追求极其简单而普通,但是,真正要做到这一切,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西戎先生在那个时代却已经做到了。这正是我们这些文学后生晚辈钦佩他的地方。正如他的同乡、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书法家、诗人段云先生给他写的一首诗,云:“劲风立绝壁,风雪傲银空。群艳知何处?茫茫见苍松。”
五
参观完西戎文学纪念馆,临出院门时,我在心里默默地向斜对面先生高大的雕像鞠了三躬,才随人群缓缓地走到不远处,上了大巴车。在大巴车上,我默默地打开手机,翻看着刚才在纪念馆里拍的一幅幅照片,默默地读着他的那些书法作品里的诗句,“半生磨砚已白头,安坐书斋再无求。手中已搁生华笔,闲读怡养守穷庐。”,“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望月披云笑一声。”,“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睛。松柏老而健,芝兰香且清。笔下文章润,山中雨露浓。夕阳无限好,霜叶满阶红。”关上手机,我回味着先生写这些诗句的时候的心境与心情,望着车窗外满世界充满翠绿和点点黄色山花的浩大吕梁山,默默地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