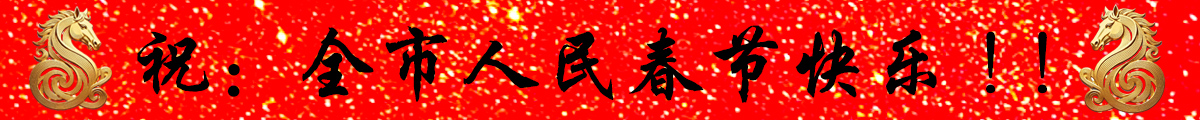春节春节
□ 李亚飞
春节,是人们祈求上苍赐予新的一年健康平安的节日。神奇的是,人们还真就在一刹那健康了,平安了。你从眼望见的所有人,他们的眼睛里放射出的,与往日截然不同的光,你从那些随处而来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他们的祝福与善意,春节就这样,在人们的相互鼓励下,在家家户户的张灯结彩里,在心田、在故乡,为所有人铺好了崭新的明天。
春节这一天的喜庆是带着一种缱绻的乡愁的。我爷爷皴裂的手掌悉悉簌簌活泛身体时,正是天麻亮的时分,我们几个孙辈的孩顽儿跟着他,给灶神、门神等神仙们磕头,香三根,裱薄薄几张,烧起的火焰印着一个背脊佝偻的老头。起初我们应该是被这仪式所震撼的,觉得新鲜好玩又带了些神圣的况味,后来长至十来岁时,竟觉得还真是麻烦得紧,好像荒废了我们的什么似的,我们无非是要放几个响亮的炮仗罢了,无非是要挨着各家跑,等着人家夸我们的新衣裳,等着人家给我们几个糖,无非是期盼着把口袋里的几块钱花出去,再灰溜溜地回家来。现在想想,那金灿灿的时光永远地过去了,留下一脑袋金灿灿的笑颜,和一个人独酌清凉的况境。木心先生在他的作品里写道:节日还是一个人过得好,要是嘻嘻闹闹的,恐怕是暴殄糟蹋了节日的。想来这话是对艺术的宣誓,也是对生活的宣战,一个人从来不必忍受什么,只有老老实实和自己待下去,耗下去,下去了,再爬上来,万丈深渊同样是晴空万里。
说起来还真是奇怪,节日就这么一天,人们竟肯耗费着许多日子来为这一日加持,仿若这日子被附着了吸附日子的魔力,只有正日子的到来,人们才好把一颗悬着的心搁置下来。还真是,不到时分,母亲是不叫我们穿新衣裳的。新衣裳是被锁在扣箱里头的,我们直盼着腊月快尽,可腊月是最麻烦的,女眷大人们是成天地聚集在火炕上,鞋底子就是在火炕上焙好的。鞋底子是老麻绳一寸一寸栓出来的,等着肥皂画好样子,熬成的面糊一层再一层像刷墙一样刷一层,再贴一层焙硬了的鞋底,等着鞋样子铰得周周正正,鞋面和鞋底再要粗麻绳紧紧地从里头固定一圈,所有人脚踩的鞋子都是这样一针一脚纳出来的。腊月里走乡窜巷的老商农们一时间多了起来,老远地便能听到他们唱调,孩芽们学这唱调是一绝,家里扯开嗓子一唱,引逗一家人都笑开,又欢快地跑大门外去了。大人们用今年收成的玉米啊、黄豆啊、土豆啊换来对方的棉花啊、豆腐啊、布啊或者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即至初一早上一醒来,新棉袄新棉裤像是一下子变出来的,在脚边摞得像座小山,甚至能闻到里头新棉花的味道。母亲啊,给她的孩子们把个子拔了又拔,衣裳挨个地穿齐整了,脸上晕出了微汗的红晕,这时候的母亲可真是好看!这一天也是很快就黑了下去,今日茹素,一年百无禁忌,大人们收拾熨帖照例是要打牌的,我们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反正是,这一天终将要在睡梦中迎来初二的太阳。初二总是有太阳的,即便下雪。
春节在我记忆里好像还真没有下过雪,童年的雪总是在悄无声息中下来的,一觉醒来才是一场老雪,我们又要在雪里作害了,不过新蒸上月家大人们是不会斥责的。我们就在雪里踩出一串串拖拉机碾过的脚印,我是后来才知道雪的秘密,不论下不下雪,母亲总要带着我们度过那些史诗般的岁月。我们都要攒着一股子劲儿,向着某种永恒作别,向着一个簇新的日子展望,我们终将要向着全新的生活完成对自我的救赎,即,沿着母亲的路,一个人朝着大雪纷飞的白茫茫处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