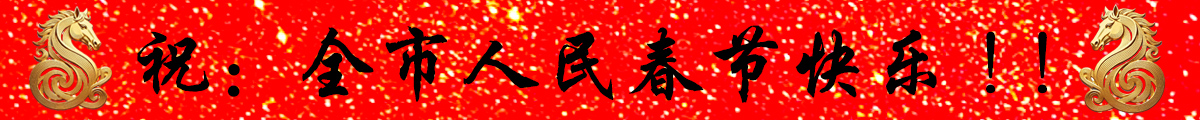如果能不睡觉(组诗)
□ 李峰
如果能不睡觉
夜越深,梦越重。深夜里的梦,就把我带入
另一个人间。在梦中,父亲在老屋,用铁丝扎着灯笼架子
然后,用大红的粉帘纸,糊上去。在门洞底,灯笼亮了
照着父亲手背上的青筋,铁丝一般。忽然,灯灭了,我在
医院,乘着月光,把父亲推上了一辆救护车。再后来,
父亲就活在一盏灯笼和一袭月光里,一明一暗。有几次,我梦见
在街头闹社火的人群中,父亲的肩上,一会坐着我,一会儿
坐着我的女儿,仿佛我们也是一个社火的表演节目。父亲一边
在人群中穿行,一边嘴里念着:十四十五游百病。很快,女儿
又坐在我的肩上,父亲却躺在了病床上,眼神像社火的尾声
天快亮了,我梦见,我从一座悬崖上跳了下去,飘飘然中
能看见远方一盏一盏的红灯笼,还有闹社火的队伍。一身冷汗中,我想
如果能不睡觉,就不做梦。在月光和社火里,我还能找到父亲吗?
无端
石头缝隙里,突然就生长出一株小草,嫩绿色的
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也无法将它与石头放在同一个视线里
或许,夹缝就是它的大地,就是它的奶娘。在荒野上
拾到一截树枝,模样像一个人,只是被风吹日晒
样子有些粗糙。暴尸荒野也是一种存世的形态,至少
生死都光明磊落。散步中,忽然就走进一个胡同,人间
顿时就不再嘈杂。看到一辆骑得破旧的自行车,就能
看出活着不过就是风尘仆仆。胡同的另一头,就又是一条大街了
我就折回来,又钻进另一条胡同。不是探秘,只是逃避
不年不节的,又有人放炮了,或添丁或娶亲或上梁或升职
一定是喜事。隐约在远处,传来哀乐,或丧夫或丧妻或夭折或
祭祀,没有固定的时分。无端的事端,看起来,都是那么荒唐
演员
我最讨厌,照相的时候,摄影师对我说
笑一笑,双脚开叉,胸部前倾,脸部向左倾斜
四十五度。后来,我看戏,举起鞭子,踮起一只脚
就是策马奔跑。双眼瞪圆,髯口抖动,就是愤怒
而最直观的是白脸,那一定是个奸臣。再后来,我看
影视剧,热恋时的接吻,不情愿,也必须亲出一腔
欲望。如果角色需要,就必须在脸上雕刻岁月的风霜
拧松关节上的螺丝,或者,干脆从生演到死。印象
最深刻的是一对情人,女子一只手,紧抱着男子,深深地
接吻中,另一只手,掏出一把刀,从背后刺向男子。那一瞬间,我
一下就看清了,爱和恨的正面与反面,阳光的温暖与灼伤
这么多年,我总觉得身边一直就有一个跟拍的摄影师
一会让我演黑脸,一会让我演白脸。直到曲终人散
卸掉妆时,脸上总是热辣辣的疼,有时像温暖,有时像灼伤
身份证
我一直相信,我的身份证,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变
正如它的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位数“X”。那时,杏花
开了,我就来到杏花村,在一片杏园中,等一场春雨,等
一个叫杜牧的诗人。那会儿,我的身份证的时间,就是
清明前后,那个“X”就是一位诗人。夜深了,在梦中
我梦见了缝纫机前给我做衣服的母亲,还有被我
骑在肩上,看社火的父亲。清冷的月光下,我能看清我的
身份号中间的那几位数:19631203。它就像一颗
月亮或一颗恒星,印在天幕上,而最后的那个“X”,是
扑簌簌掉着没完的眼泪。有时候,我把身份证的
号码,反扣过。那样,就看见我头上的白发,眼角的
皱纹,就忘记了我的年龄,忘记了在有效期内,与杜牧的
几次擦肩而过,还有父母生我的那个刻骨铭心的日期
因此,有时,我把“X”求证为杜牧;有时,把“X”求证为眼泪
更多的时候,我把它求证为遗忘或不能忘却的思念
后来,我只相信,“X”就只等于19631203,这个数字是“X”的
心脏。X等于Y时,我正在与杜牧饮酒作诗,或做梦
高兴
立春了,一只麻雀来到枣树上,它抬头鸣叫时
太阳光刚好照在它的小嘴尖上,它是第一个亲吻
春天的,我一笑时,它就鸣个不停;小河边的荒草
在风中摆动,它们并没有枯死,而是被风摇醒
与春天的约定,就是不停地摇摆。它们不仅要
在春风中醒来,还要把河水摇醒,让流动的水声
把我也喊醒,我一笑,河流两岸就都醒了
那些麻雀的鸟屎,有时候,会刚好落在我的头顶
暖暖的,像一双小手。也有几片绒绒的羽毛,飘了下来
我放在手心里,就像捧着一个暖洋洋的春天;我漫步在
小河边时,那些荒草就摇得更加起劲,像一群
顽皮的孩子,在河岸上奔走。此时,那条河水刚刚融化
清清冽冽地流动着,像有人在我的心中,轻轻地
拨动着春天的竖琴。我再一笑,一个春天就来了
在初春,高兴的不是桃花红杏花白,而是悄悄萌动的春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