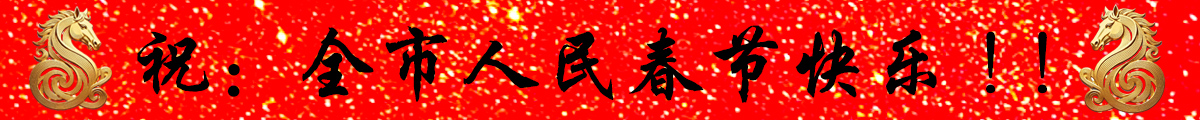访后寺上
□ 边草
忘了之前来过多少回,这次却是专程来访,同行的还有三个人,网络高手建军、农民记者锦云、文化局老局长高伍平。建军本是学历史的,锦云热衷于地方史料的探寻整理,高局是极精熟《临县志》的老师。
车在高速上疾驰,高局老师滔滔不绝,讲说关于临县的点点滴滴。我接连两个早晨起太早,中午又喝了点酒,抑制不住的打瞌睡,一路听来断断续续、模模糊糊。
很快就到八堡了,再往北十里就是后寺上。车在山脚下的泉水边停好,抬头看时,看管老杨已经在山腰的庙宇前等着了。
锦云下车便急赶着拍照。我站定了仔细看,多少年了,这却是第一次认真地看,感觉有些愧疚,之前竟没有过一次用心。建筑依山就势,窑洞层叠错落,半壁上大小三个石窟一字排开,对面是一堆奇特的乱石,乱石东南一座戏台,西南一座石房,坍塌破败。时节正是四五月,圪针葳蕤,蜜蜂嘤嘤嗡嗡,空气里丝丝缕缕全是枣花香。
关于后寺上,翻遍《临县志》,并无一字记载,很是奇怪。这些建筑由来已久,虽不算庞大但也不算小,单单这几个石窟,在县内就实属罕见,如此稀罕之处,史官们怎么就能视而不见?在后来的地方书籍里,也只有郭时键《临县寺院概论》里这样讲:八堡曹家沟上面,有龙泉寺……近年来,有人又取名为天王寺。八堡村有寺圪垯、前寺湾、中寺湾、后寺湾等地名,原有寺院,今已毁而不存。人们又称寺圪垯的寺为前寺上,称龙泉寺为后寺上。
八堡村有寺圪垯、前寺湾、中寺湾、后寺湾等地名,不假,现在仍在沿用。寺圪垯原有寺院,老人们也有传说,寺院叫兴佛寺,规模曾超过佳县白云山,后来逐步被毁,兴佛寺有下设寺院,一处便是后寺上,另一处是后寺上斜对面的佛堂寺。郭时键所讲前寺上、后寺上的说法可信,有理据。只是,这前寺上有个正式的名号“兴佛寺”,后寺上呢?如果也有,那该是龙泉寺,还是天王寺?
很快我又更加迷糊了。随着看管老杨来到山腰的庙宇前,在通往庭院的山门洞顶,赫然镶嵌着一块古旧的石匾,上书:龙泉庵;而山门洞顶的后面,又是另一块石匾,同样古旧,上书:天王祠。一座庙宇,前后两块石匾,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名号,而且差别如此之大:一个“庵”,一个“祠”,庵里供奉着神佛,住着尼姑,而祠里应该是供奉先祖圣人的,住着的不会是女子。我的头大了,眼睛望向高局老师,高局老师一言不发,只顾在山门洞前的石圪台上坐着。我问看管老杨,老杨说这两块石匾原来闲置在院子的角落里,九一年修缮时,他觉得石匾古旧有价值,就把它们镶嵌在了现在的位置。石匾不会假,这说明古时候“龙泉庵”和“天王祠”的叫法是有的。水越搅越浑,龙泉寺,龙泉庵,天王寺,天王祠,我到底该叫它什么?
我在庙宇里仔细搜寻,希望可以发现点什么。这是个极讲究的小院,坐北朝南,干净整洁,上下左右的窑洞围起来,宽约10米,长约15米。窑洞都是新砌的石口子,每个窑洞里都是新塑的神像、新涂的壁画。从山门进,左右窑里供奉着四大天王,廊道里竖着三块石碑,上刻九一年修缮庙宇时积善款者的名字,石碑后面一个石香炉,极简单,像灯台,年代久了,风雨剥蚀得很是沧桑。廊道两边各栽着四株侧柏,小胳膊粗细,两米余高,虽然少,但也成排,很规整。柏树后面,东西两侧的耳房里,分别供奉着龙王、土地、观音、二郎真君和十八罗汉。正面是正殿,三孔窑,正中供奉着释迦牟尼佛,东西两边分别是清净化身佛和圆满报身佛。正殿窑里存放着三四块方形石碑,上面刻着清道光八年修缮庙宇以及积善款者的名字,除此再无别的信息。正殿与东边耳房的犄角旮旯,长出几株野草,草丛里侧立着几截残缺断裂的石碑,翻出来看,却是风蚀得没有了半点字迹。
庙宇里寻不到答案,我只有转出来再问看管老杨,我们的问答足足有一麻袋多,但有价值的微乎其微。老杨说,据传山下原来有过一个尼姑庵,后来庵里的尼姑“不行好”(与人发生苟且之事),被村民们驱逐了。我向山脚望下去,山泉还在,泉边的老柳树也在。记得小时候来看戏,爬在山泉边喝水,泉水清冽甘甜。如果传说可信,山泉边上一座庵,“龙泉庵”是可以理解了。“天王祠”呢?百度里搜一搜,全国各地供奉四大天王的处所数以万千计,天王寺、天王殿、天王庙,哪里有叫天王祠的?而且这样的庙宇里大多是专供四大天王的,眼前这里,四大天王却在下房两侧,不在正殿,并非主神。我想起以前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好像在山西北部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天王祠,里面供奉的不是四大天王,只一个人,托塔天王李靖。难道这个天王祠里,原来也只是供奉着天王李靖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想来想去只能做这样的猜测:后寺上是一个综合佛教场所,从山脚到山腰是一个建筑群,山脚下有龙泉庵,半壁上有十佛洞、百佛洞、千佛洞、万佛洞,山腰的庙宇不止一祠一庙一殿,由若干个部分组成,石匾所名的天王祠只是其中之一。龙泉寺和天王寺的叫法,犯以点带面之错,而且还错在字面混淆、谐音讹传。这样想过之后,突然觉得悲戚,感觉后寺上就像一个被佛国遗弃的孩子,搁置在这荒郊野外,无家可归,不知姓甚,不知名谁。
从庙宇下来,钻进石窟。后寺上最吸引人的还是这几个石窟,悬在山体半壁上,口朝南,从东到西,一字排开。石窟大小不一,分别叫作十佛洞、百佛洞、千佛洞。还有一个叫万佛洞,最大,在东边半壁上,口朝西,“一打三反”时候被一炮炸毁了,现在只留下一堆乱石、万千遗憾。
石窟何年何月为何人所开,没有人知道,连传说里也找不到一点影子。我闭上眼睛,猜想当时候的情景,是否也如乐樽和尚初到敦煌,山头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老和尚慈眉善目、须髯飘飘。开山凿窟,只有锤錾,那该是一场怎样浩荡而旷日持久的工程,耳畔是锤錾之声,一声一声,悠远铿锵。
洞窟几近方形,长、宽、高略有不同,正面入口,宽窄高低与双扇门相仿,洞顶八边形撑托,呈包状。内四壁自上而下凿出许多道石坎,每两道石砍之间水平平行、间隔均匀,接近底端变成了两道明显石阶,台状。看管老杨说,原来四壁石坎上摆满了泥塑的小佛像,底端的石台上是个头大些的,开会似的,满满当当。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来看戏,跟着外公在洞里吃饭,石坎上还零零落落摆放着三五个,现在却是一个也没有了。环顾洞顶和四壁,除了石坎石台,还有几个残缺不全、依稀可辨的石刻佛像,还有几处残留的泥皮壁画,大的如盆底,小的如巴掌,图案虽已残缺,但线条依然清晰,色彩依然鲜艳。锦云不停地长吁短叹,踮起脚抚摸石坎,端起相机拍下每一处残存。
要回去了,大家心里都很沉重。锦云又去拍万佛洞,我站在山脚远远地望着他,看他背着相机艰难地从那一堆乱石中间爬上去,爬一段拍一下,感觉就像看法医尸检被害的亲人。那“轰隆”一声巨响,永世再无法回转的坍塌。我在心里敬畏那万千只壁虎,用孱弱的身躯护住了哪怕早已经惨死了的洞窟,眼前血肉模糊。
终于还是不能叫出“后寺上”的名字。在这前后不着村落的荒野里,背后一座大山,面前一条长河,山光秃秃的苍凉,水滔滔不绝昼夜如斯。我不由得闭上眼睛,我总是这样,不知是逃避,是祭奠,还是想要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