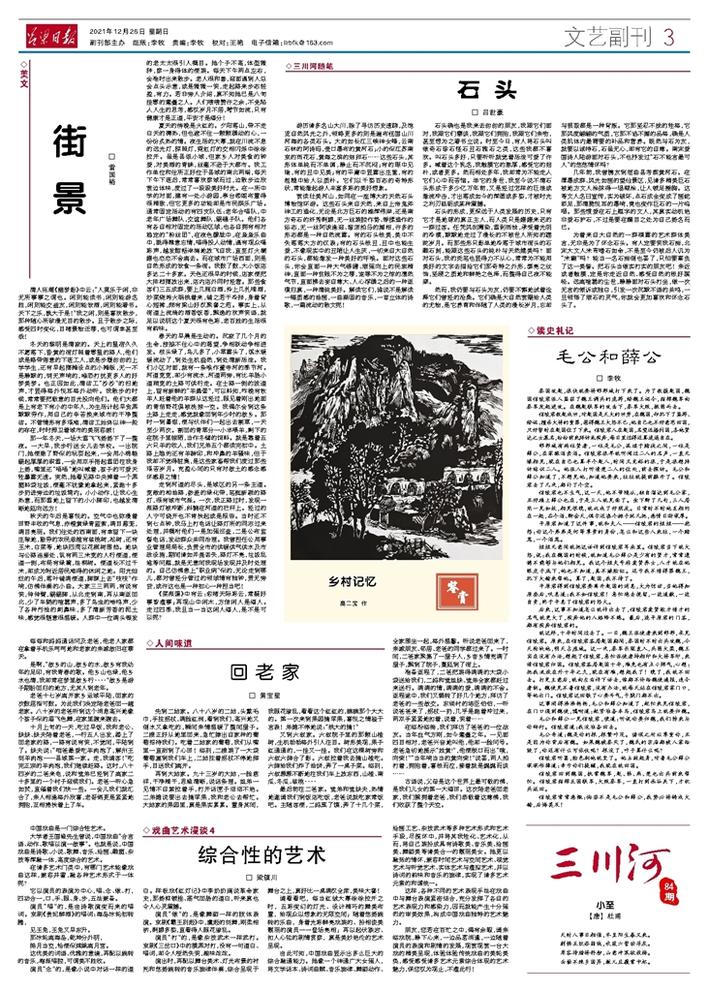游历诸多名山大川,除了寻访历史遗踪,及饱览自然风光之外,领略更多的则是遍布祖国山川河海的各类石头。大的如长江三峡神女峰,云南石林的阿诗玛,壶口瀑布的黄河石;小的似江苏南京的雨花石,黄海之滨的细卵石……这些石头,其形体单纯而不单调,静止而不沉闷;有的瑕中见瑜,有的丑中见美;有的平庸中显露出庄重,有的粗糙中给人以质朴。它们以千姿百态的奇特形状,常能激起游人丰富多彩的美好想象。
赏读壮美河山,如同在一座博大的天然石头博物馆环游。这些石头来自天然,来自上帝鬼斧神工的造化,无论是北方巨石的雄浑伟岸,还是南方奇石的纤秀婀娜,无一丝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俗态,无一丝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的媚相,许多的形态都是一种自然流露。有的石头极美,美中不失落落大方的仪表;有的石头极丑,丑中也能生爱,不像现实中的丑陋让人生厌,一切来自大自然的石头,都能激发一种美好的呼唤。面对这些石头,你会直面一种大气磅礴、顽强向上的民族精神,直面一种贫贱不为之移,宠辱不为之惊的凛然气节,直面拂去妄自尊大、人心浮躁之后的一种返璞归真,一种清纯美好。解读它们,谁说不是解读一幅质感的油画,一曲凝固的音乐,一首立体的诗歌,一篇流动的散文呢!
石头确也是我来去匆匆的朋友,我跟它们面对,我跟它们攀谈,我跟它们拥抱,我跟它们亲吻,甚至想为之著书立说。时至今日,有人将石头叫做奇石珍石怪石丑石雅石之类,这些我都不喜欢。叫石头多好,只要听听就觉着活泼可爱了许多。喊着这个乳名,我触摸它的憨厚,感受它的拙朴,或者更多。然而相处多年,我却常为不能走入它们心中而苦恼。举它的身世,我至今说不清石头形成于多少亿万年前,又是经过怎样的巨浪或激流冲击,才出落成如今的浑圆或多姿,才被时光之利刃砥砺成某种震撼。
石头的形成,更深远于人类发展的历史,只有它才是地球的真正主人,而人类只是姗姗来迟的一群过客。任凭风刮霜染,雪剥雨蚀,承受着光阴的冷漠,默默地走过了漫长的不被世人所知的蹉跎岁月。而那些形只影单地冷落于城市街头的石雕石刻,能跟这些石头的纯朴与天然媲美吗?面对石头,我的秃笔也显得力不从心,常常为不能用美好的文字去描绘它们那奇特之外形,漂亮之纹饰,坚硬之质地和鲜艳之色泽,而整得自己夜不能寐。
然而,我仍要与石头为友,仍要不懈地试着诠释它们曾经的沧桑。它们确是大自然赏赐给人类的尤物,是它养育和伴随了人类的漫长岁月,忘却与损毁都是一种背叛。它那坚忍不拔的性格,它那风度翩翩的气质,它那不谄不媚的品格,确是人类肌体内最需要的补品和营养。既然与石为友,就要以诚待石,石虽无心,却有它的自尊。南宋爱国诗人陆游面对石头,不也抒发过“石不能言最可人”的悠悠情怀吗?
几年前,我曾携友到垣曲县考察黄河石。在潭瀑成群、风光如画的望仙景区,见诸多精美巨石被地方文人涂抹得一塌糊涂,让人顿足捶胸。这等文人名曰宣传,实为破坏,点石成金变成了画蛇添足,那清脆悦耳的瀑响,竟也变作巨石的一片呜咽。那些惯爱在石上题字的文人,其真实动机绝非爱石护石,不过是要在醒目之处为自己扬名而已。
为着来自大自然的一群裸露的艺术群体美言,无非是为了怀念石头。有人定要笑我石痴,北宋大文人米芾嗜石如命,不是至今仍被后人讥为“米癫”吗?能当一名石痴倒也罢了,只怕要辜负了这一美誉。把石头当做实打实的朋友吧!亲近或者触摸,定是你走近自然、感受自然的极好蹊径。远离喧嚣的尘世,静静面对石头打坐,做一次无言的倾诉或独白,引发一次沉默不语的共鸣,一旦领悟了顽石的灵气,你就会更加喜欢和怀念石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