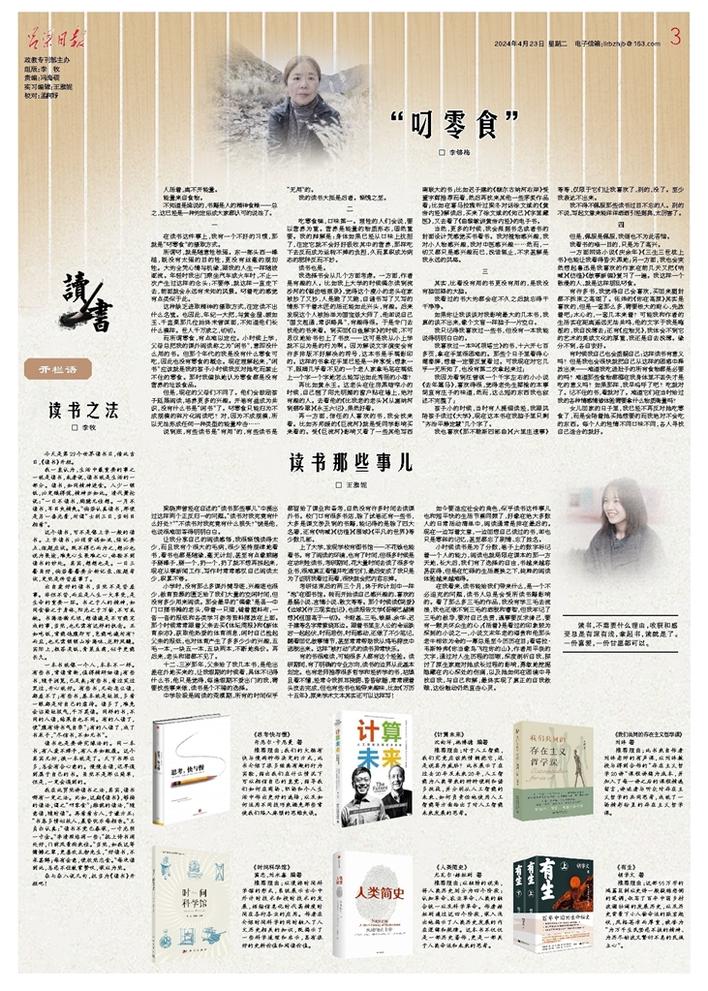人活着,离不开能量。
能量来自食物。
不知道是谁说的,书籍是人的精神食粮——总之,这已经是一种约定俗成大家都认可的说法了。
一
在读书这件事上,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叼零食”的摄取方式。
所谓叼,就是随意性极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既没有太强的目的性,更没有丝毫的规划性。大约全凭心情与机缘,跟我的人生一样随波逐流。年轻时我出门乘坐汽车或火车时,不止一次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不要停,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前面就会永远有未知的风景。叼着吃的感觉有点类似于此。
这种缺乏进取精神的摄取方式,注定读不出什么名堂。也因此,年纪一大把,与黄金屋、颜如玉、千盅粟那几位始终未曾谋面,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模样。世人千万戒之,切切。
而所谓零食,有点难以定位。小时候上学,父母总把我的课外阅读称之为“闲书”,意即没什么用的书。但那个年代的我是没有什么零食可吃,因此也没有零食的概念。现在理解起来,“闲书”应该就是我的孩子小时候我反对她吃而禁止不住的零食。那时我偏执地认为零食都是没有营养的垃圾食品。
但是,现在的父母们不同了。他们会鼓励孩子延展阅读,培养更多的兴趣。开卷有益成为共识,没有什么书是“闲书”了。叼零食只能归为不成规模的碎片化阅读吧?对,因为不成规模,所以无法形成任何一种类型的能量冲击……
说到底,有些读书是“有用”的,有些读书是“无用”的。
我的读书大抵是后者。惭愧之至。
二
吃零食嘛,口味第一。理性的人们会说,要以营养为重。营养是能量的物质形态,固然重要。我的辩解是:身体如果已经从口味上抗拒了,注定它就不会好好吸收其中的营养,那样吃下去反而成为运转不掉的负担,久而累积成为病态的肥胖反而不妙。
读书也是。
我选择书会从几个方面考虑。一方面,作者是有趣的人。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偶尔读到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觉得这个瘦小的老头在家被抄了又抄,人是跪了又跪,自谴书写了又写的情形下干着木匠的活还能如此兴头,有趣。后来发现这个人被抬举为国宝级大师了,他却说自己“国文粗通,常识略具”,有趣得很。于是专门去找他的书来看。到买回《白鱼解字》的时候,不可思议地给书包上了书皮——这可是我从小上学就不以为是的行为啊。因为解说文字演变会有许多排版不好解决的符号,这本书是手稿影印的。这样的书拿在手里已经是一种享受:想象一下,眼睛几乎看不见的一个老人家拿毛笔在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怎么能写出如此秀丽的小楷?
再比如黄永玉。这老头在住房黑暗窄小的时候,自己画了阳光明媚的窗户贴在墙上,绝对有趣的人。去看他的《比我老的老头》《从塞纳河到翡冷翠》《永玉六记》,果然好看。
再一方面,信任的人喜欢的书,我会找来看。比如齐邦媛的《巨流河》就是受同学影响买来看的。受《巨流河》影响又看了一些其他写西南联大的书;比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受董宇辉推荐而看,然后再找来其他一些茅奖作品看;比如在喜马拉雅听过梁冬对话徐文斌的《黄帝内经》解读后,买来了徐文斌的《知己》《字里藏医》,又去看了《曲黎敏讲黄帝内经》的电子书。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根据书名或者书的封面设计凭感觉买书看书。我对植物感兴趣,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对中医感兴趣……然而,一切又都只是感兴趣而已,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是我永远的风格。
三
其实,比看没有用的书更没有用的,是我没有脑回路的大脑。
我看过的书大约都会在不久之后就忘得干干净净。
如果你让我谈谈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我真的谈不出来,像个文盲一样脑子一片空白。
我只记得我喜欢过一些书,但没有一本我能说得明明白白的。
我喜欢过一本叫《项塔兰》的书,十六开七百多页,拿在手里很困难的。那些个日子里看得心潮澎湃,想着一定要反复看过。可我现在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了,也没有第二次拿起来过;
我因为看到汪曾祺一个千字左右的小小说《去年属马》,喜欢得很,觉得老先生揶揄的本事简直有庄子的味道,然而,这么短的东西我也叙述不完整了;
孩子小的时候,当时有人提倡读经,我跟风陪孩子读过《大学》,现在这本书在我脑子里只剩“齐治平静定慧”几个字了。
我也喜欢《那不勒斯四部曲》《六里庄遗事》等等,仅限于它们让我喜欢了,别的,没了。至少我表达不出来。
我不得不佩服那些读书过目不忘的人。别的不说,写起文章来能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太厉害了。
四
但是,佩服是佩服,我倒也不为此苦恼。
我看书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高兴。
一方面网络小说《庆余年》《三生三世枕上书》也能让我看得昏天黑地;另一方面,我也会突然想起鲁迅是我喜欢的作家在前几天又把《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复习了一遍。我这样一个散漫的人,就是这样胡乱叼食。
有许多书,我觉得自己会喜欢,买回来塑封都不拆束之高阁了。张炜的《你在高原》其实是喜欢的,但是一套那么多,需要极大的耐心,先放着吧;木心的,一套几本来着?可能我和作者的生活实在距离遥远无法共鸣,他的文字于我是晦涩的,我自浅薄去;还有《应物兄》,我体会不到它的艺术的美或文化的厚重,我还是自去浅薄。缘分不到,各自安好。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质疑自己:这样读书有意义吗?但是我也会很快就把自己从这样的困惑中释放出来——难道我吃进肚子的所有食物都是必要的吗?难道那些食物都囤在我身体里不丢失才是吃的意义吗?如果那样,我早呜呼了吧?吃就对了。记不住的书,看就对了。难道它们在当时给过我的各种情感情绪体验需要拿什么物质衡量吗?
女儿回家的日子里,我已经不再反对她吃零食了,而是会陪着她买她想要的而我绝对不会吃的东西。每个人的性情不同口味不同,各人寻找自己适合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