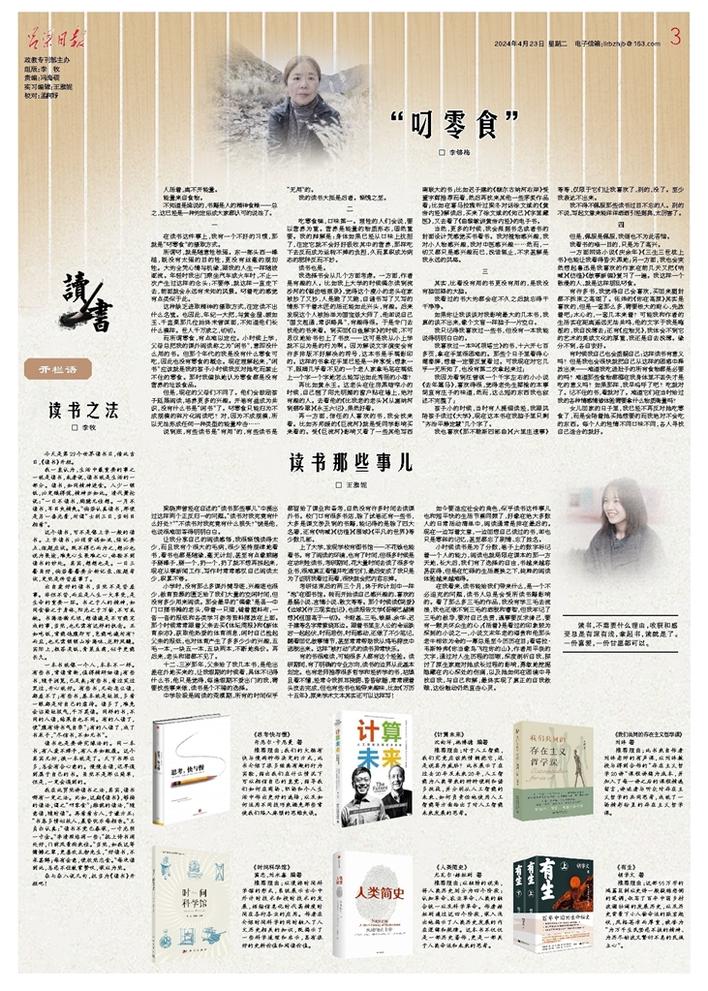梁晓声曾经在自述的“读书那些事儿”中提出过这样两个正反归一的问题。“读书对我究竟有什么好处?”“不读书对我究竟有什么损失?”饶是他,也说很难回答得明明白白。
让我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悟,我很惭愧读得太少,而且我有个很大的毛病,很少坚持规律地看书,看书也都是随缘,毫无计划,甚至有点像熊瞎子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扔了就不想再拣起来,现在从事新闻工作,写作时常常感叹自己阅读太少,积累不够。
小学时,没有那么多课外辅导班,兴趣班也很少,教育资源的匮乏给了我们大量的空闲时间,但没有多少用来阅读。那会最早的“偶像”是县一中门口摆书摊的老头,带着一只猫,铺着塑料布,一沓一沓的报纸和各类学习参考资料摆放在上面。那个时候常常跟着父亲去买《体坛周报》和《新体育杂志》,获取他热爱的体育消息,闲时自己捡起父亲的报纸,也对体育产生了多多少少的兴趣,五毛一本,一块五一本,五块两本,不断地涨价。再后来,老头和猫都不见了。
十二、三岁那年,父亲给了我几本书,是他出差在外地买来的,让我假期的时候看,具体不记得什么书,他只是觉得,每逢假期不爱出门的我,需要找些事来做,读书是个不错的选择。
中学阶段是阅读的荒漠期,所有的时间似乎都留给了课业和备考,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校门口有很多书店,除了试卷还有一些书,大多是课文涉及到的书籍,能记得的是除了四大名著,还有《呐喊》《彷徨》《围城》《平凡的世界》等少数几部。
上了大学,发现学校有图书馆——不花钱也能看书。有了阅读的环境,也有了时间,但很多时候是在功利性读书,考研期间,花大量时间去读了很多专业书,很难真正看懂并吃透它们,最后变成了我只是为了证明我看过而看,很快就会把内容忘掉。
考研结束后的两三个月,终于和计划中一样“泡”在图书馆。转而开始读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悬疑小说、言情小说、散文等等。那个时候读《简爱》《边城》《许三观卖血记》,也读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祖国高于一切》。卡耐基、三毛、铁凝、余华、迟子建等名字常萦绕耳边。跟着书里主人公的命运跌宕一起起伏,时而悲伤,时而感动,还做了不少笔记,翻看回忆故事情节,甚至常常帮助我从鸡毛蒜皮中逃脱出来。这样“被打动”式的读书异常快乐。
有的书很难读,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读研期间,有了明确的专业方向,读书的边界从此基本划定。也有老师推荐很多哲学和经济学的书,枯燥且看不懂,经常令我抓耳挠腮、昏昏欲睡,常常硬着头皮去完成,但也有些书也能带来趣味,比如《万历十五年》,原来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
如今要适应社会的角色,似乎读书这件事儿也和短平快的生活节奏同频了,好像在绝大多数人的日常活动清单中,阅读通常是排在最后的。现在一边写着文章,一边回想自己读过的书,却也只是零碎的记忆,甚至都忘了剧情、忘了姓名。
小时候读书是为了分数,卷子上的数字标记着一个人的能力,阅读也就局限在课本的那一方天地,长大后,我们有了选择的自由,书越来越容易获得,但是在忙碌的生活裹挟之下,纯粹的阅读体验越来越难得。
在我看来,读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一个不必追究的问题,读书人总是会受所读书籍影响的。看了那么多三毛的作品,我没有学三毛去流浪,我也还做不到三毛的洒脱和睿智,但我牢记了三毛的教导,要对自己负责,遇事要反求诸己,要有一颗关怀众生的心;《活着》是看过的印象较为深刻的小说之一,小说文末年老的福贵和他那头老牛相依为命的一幕总是至今历历在目;看塔拉·韦斯特弗《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用平淡的文字,通过对人生历程的回顾,深度剖析自我,探讨了原生家庭对她成长过程的影响,勇敢地挖掘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伤痛,以及她如何在困境中寻找自我,与自己和解,最终实现了真正的自我救赎,这份触动仍然直击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