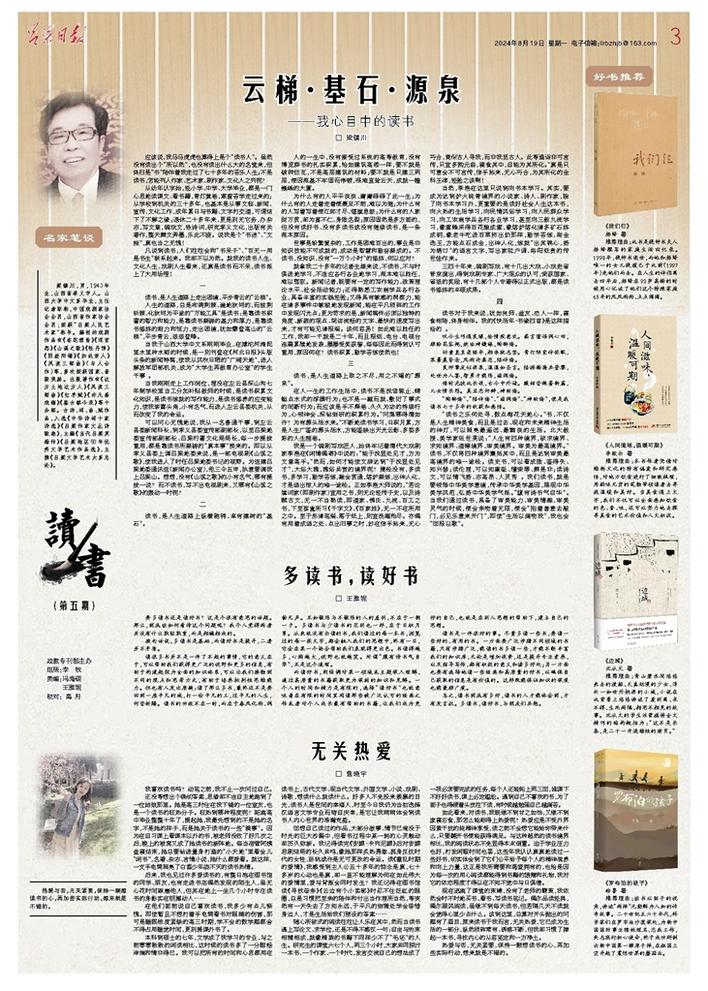□ 梁镇川
应该说,我马马虎虎也算得上是个“读书人”。虽然没有读出个“所以然”,也没有读出什么大的名堂来,但终归是“书”陪伴着我走过了七十多年的苦乐人生;不是读书,怎能列入作家、艺术家、剧作家、文化人之列呢?
从幼年认字始,经小学、中学、大学毕业,都是一门心思地读课文、看书藉,青灯黄卷,寒窗苦学走过来的;从学校到机关的三十多年,也基本是从事文秘、新闻、宣传、文化工作,成年累日与书籍、文字打交道,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退休二十多年来,更是别无它务,办杂志,写文章,编戏文,咏诗词,研究孝义文化,出版有关著作,整天舞文弄墨,乐此不疲。说我是个“书迷”、“文痴”,真也当之无愧!
凡说到读书,人们往往会和“书呆子”、“百无一用是书生”联系起来。我却不以为然。就我的读书人生、文化人生、戏剧人生看来,还真是读书而不呆,读书派上了大用场哩!
一
读书,是人生道路上走出困境、平步青云的“云梯”。
人生的道路,总是布满荆棘、遍地坎坷的,而披荆斩棘、化坎坷为平途的“万能工具”是读书:是靠读书积蓄的智力和能力,是靠读书凝铸的基力和厚力,是靠读书修炼的耐力和恒力,走出困境,犹如攀登高山的“云梯”,平步青云,级级登峰。
当我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刚刚毕业,在滹沱河滩泥里水里种水稻的时候,是一则刊登在《河北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特稿,使我从风吹日晒的“广阔天地”,进入解放军团部机关,成为“大学生再教育办公室”的学生干事 。
当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埋没在左云县深山沟七年制学校里当工分加补贴教师的时候,是读书积累文化知识,是读书练就的写作能力,是读书修养的应变能力,使我崭露头角,小有名气,而进入左云县委机关,从而改变了我的命运。
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从一名普通干事,到左云县委新闻科长,到孝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以至吕梁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吕梁行署文化局局长,每一步提拔重用,都是靠读书所凝铸的“真本事”换来的。即以从孝义县委上调吕梁地委来说,是一部电视剧《山溪之歌》,使我进入了时任吕梁地委书记的视野。为组建吕梁地委通讯组(新闻办公室),他三令五申,执意要调我上吕梁山。想想,没有《山溪之歌》的小有名气,哪有提拔一说?而不读书,写不出电视剧来,又哪有《山溪之歌》的轰动一时呢?
二
读书,是人生道路上纵横驰骋、卓有建树的“基石”。
人的一生中,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没有博览群书的扎实积累,恰如建筑高楼一样,要不就是破砖烂瓦,不是高层建筑的材料;要不就是只建三两层,便因根基不牢固而停顿,很难直耸云天,成就—幢巍峨的大厦。
为什么有的人平平淡淡、庸庸碌碌了此一生;为什么有的人走着走着便裹足不前,难以为继;为什么有的人写着写着便江郎才尽、偃旗息鼓;为什么有的人家财万贯,却为富不仁、身败名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没有读好书、没有多读书或没有继续读书,是一条根本原因。
世事是纷繁复杂的,工作是困难百出的,事业是非知识技能不可成就的,成功是智慧和勤奋凝成的。不读书,没知识,没有“一万个小时”的修炼,何以应对?
就拿我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来说,不读书,不与时俱进地学习,不适应各行各业地学习,根本难以胜任,难以驾驭。新闻记者,既要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政策理论水平、社会活动能力;还得熟悉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得具有敏感的洞察力,能在诸多事件中敏锐地发现新闻,能在平凡琐碎的工作中发现闪光点;更为苛求的是,新闻稿件必须以独特的角度、新颖的观点、简洁流畅的文字、最快的速度写出来,才有可能见诸报端。谈何容易!如此难以胜任的工作,我却一干就是二十年,而且报纸、电台、电视台连篇累牍地发表,屡屡受奖获誉,每每因此而得到认可重用,原因何在?读书积累,勤学苦练使然也!
三
读书,是人生道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在人一生的工作生活中,读书不是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式的浮躁行为;也不是一蹴而就、敷衍了事式的间断行为;而应该是手不释卷、久久为功的持续行为,心领神会、深钻细研的积累行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断地读书学习,日积月累,方是人生广鉴的源头活水,方能鉴映出天光云影、多姿多彩的人生画卷。
我是一个编剧写戏匠人,始终牢记着清代大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的:“能于浅显处见才,方为文章高手。”然而,如何才能使文辞达到“于浅显处见才”,大俗大雅,雅俗共赏的境界呢?捷径没有,多读书,多学习,勤学苦练,融会贯通,熔炉凝练,出神入化,才是语出惊人的唯一途径。正如李渔大师说的,“若论填词家(即剧作家)宜用之书,则无论经传子史,以及诗赋古文,无一不当熟读,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书,下至孩童所习《千字文》、《百家姓》,无一不在所用之中。至于形诸笔端、落于纸上,则宜洗濯殆尽。亦偶有用着成语之处、点出旧事之时,妙在信手拈来,无心巧合,竟似古人寻我,而非我觅古人。此等造诣非可言传,只宜多购元曲,寝食其中,自能为其所化。”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信手拈来,无心巧合,为其所化的金科玉律,经验之谈啊!
当然,李渔在这里只说到向书本学习。其实,要成为达到炉火纯青境界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除了向书本学习外,更重要的是读好社会人生这本书,向火热的生活学习,向民情风俗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学习,甚至向三教九流学习,像蜜蜂采得百花酿成蜜,像熔炉熔化诸多矿石炼成钢,像老牛吃进百草挤出奶那样,勤学苦练,淘金选玉,方能点石成金,出神入化,练就“出其锦心,扬为绣口”的语言文字,写出家弦户诵、洛阳纸贵的传世佳作来。
三四十年来,编剧写戏,有十几出大戏、小戏赴省晋京演出,得到戏剧专家、广大观众的认可,荣获国家、省级的奖励,有十几部个人专著得以正式出版,都是读书修炼的丰硕成果。
四
读书对于我来说,犹如良师、益友、恋人一样,寝食相陪,终身相伴。我的《快活年·书缘四首》是这样描绘的 。
叹今生巧遇良缘,恰情投意欢。柔言蜜语润心田,顾盼花容艳,妖冶神缱绻,陶醉俺。
幼童直至老经年,相亲犹志坚。青灯陋室伴侬眠,寒暑晨昏念,风雨沧桑恋,陪伴俺。
良师挚友似源泉,温温如圣言。陪游瀚海共登攀,处世为人鉴,智勇才能炼,滋润俺。
惜时光彼此长谈,古今中外谙。酸甜苦辣著新篇,儿女情长怨。美丑忠奸辨,神助俺。
“陶醉俺”、“陪伴俺”、“滋润俺”、“神助俺”,便是我读书七十多年的收获和感悟。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书,不仅是人生精神美食,而且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精神生活的神灯,可以照亮最遥远、最黯淡的生活。北大教授、美学家张世英说:“人生有四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审美为最高境界。”读书,不仅将四种境界囊括其中,而且是达到审美最高境界的唯一途径。读史书,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读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读诗文,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 。我们读书,就是要领悟中华美学意境,传承中华美学基因,展现中华美学风范,弘扬中华美学气派。“腹有诗书气自华”。当我们通过读书,具备了审美能力、审美情趣、审美灵气的时候,便会亲吻着无限,便会“抱着善意去敲门,必见乐意来开门”,即使“生活以痛吻我”,我也会“回报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