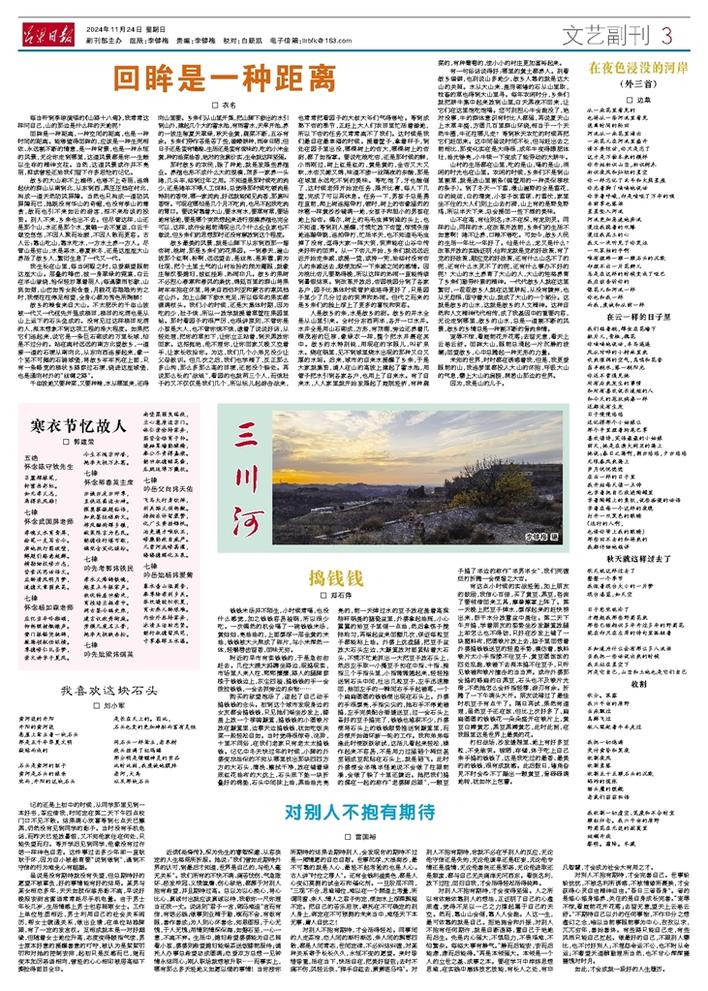每当听到李琼演唱的《山路十八弯》,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山的那边是什么样的天地呢?
回眸是一种距离,一种空间的距离,也是一种时间的距离。能够值得回眸的,应该是一种生死相依、永远割不断的情意,是一种背景,也是一种永恒的风景,无论你走到哪里,这道风景都是你一生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当然,这道风景或许并不亮丽,抑或曾经还给我们留下许多悲怆的记忆。
故乡的大山称不上雄伟,也够不上奇丽,连绵起伏的群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黑压压挡在村北,构成一道天然防风屏障。当然也只构成一道防风屏障而已,她既没有华山的奇崛,也没有泰山的尊贵,故而也引不来如云的游客,招不来洽谈的投资。别人不来,乡亲也出不去。但尽管这样,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因人聚而妆颜,不因人散而更容。古人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尽管山是穷山,水是恶水,春夏秋冬,还是这座座大山养活了故乡人,繁衍生息了一代又一代。
我生长在山里,每当闲暇之时,总爱凝望眼前这座大山。层叠的峰峦,披一身翠绿的霓裳,白云在半山缭绕,恰似轻纱罩着丽人;每遇骤雨衫歇,山岚如烟,山峦如秀女般含羞,月貌花容隐隐约约之时,我便往往停足相望,全身心都为秀色所陶醉!
故乡的粮食来自大山。不太肥沃的千亩山坡被一代又一代祖先开垦成梯田,梯田的圪塄也是从山上运下的石头垒成的。没有见过这样梯田圪塄的人,根本想象不到这项工程的浩大程度。如果把它们连起来,说它是一条巨石砌成的万里长城,怕是不过分的。站在离村远远的南方北望故乡,一道接一道的石埂从南向北,从东向西连接起来,像一个坚不可摧的石铸城堡,将故乡牢牢托在上面,只有一条略宽的梯状乡路穿过石埂,绕进这座城堡,也是通向村外的“丝绸之路”。
千亩坡地又要种菜,又要种粮,水从哪里来,还得向山里要。乡亲们从山里开渠,把山脚下渗出的水引到山外,建起几个大的蓄水池,有雨蓄水,天旱开池,养的一坡庄稼夏天翠绿,秋天金黄,蔬菜不断,五谷有余。乡亲们劳作苦是苦了些,锄耧耕种,雨淋日晒,但日子还是蛮有情趣、生活还是蛮有滋味的,吃的小米金黄,种的油菜油香,绝对的货真价实,生命就这样坚强。
那时故乡的农民,除了种地,就是发展些养殖业。养殖也形不成什么大的规模,顶多一家养一头猪,几头羊,临到过年之用。不知道是那时候吃的肉少,还是猪羊不喂人工饲料,总觉得那时候吃顿肉是特别的香呀,哪一家炖肉,好远就能闻见肉香,那真叫香呀。可现在哪怕是几个月不吃肉,也吊不起我吃肉的胃口。要说背靠着大山,要水有水,要草有草,要场地有场地,要是哪个突然想起来进行规模养殖也完全可以,这样,或许会超前涌现出几个什么企业家也不敢说,但乡亲们的思想那时还没有解放到这个程度。
故乡最美的风景,就是山脚下从东到西那一溜杏树、桃树,那是乡亲们的花果园。一到春天,遍山坡那个红啊、粉啊,远远望去,是丝帛、是彩霞,蔚为壮观,把个土里土气的山村妆扮的颇为耀眼,就像庄稼汉娶媳妇,披红挂彩,热闹非凡。故乡的果树不必担心春寒和春风的袭扰,绵延百里的群山将果树牢牢抱在怀里,将来自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寒风挡在山外。加上山脚下渗水充足,所以每年的果实都缀满枝头。我们小的时候,还是大集体时期,因为吃的少,肚子饿,所以一放学就提着草筐往果园里钻。那时看园子的很严厉,也很讲原则,不管你是小孩是大人,也不管你饿不饿,逮着了说说好话,从轻处理,把你的草扣下,让你立正站着,到天黑放你回家。这招挺绝,他不理你,让你回家又晚又空着手,让家长收拾你。为这,我们几个小弟兄没少让父母教训。但几次之后,我们也学精了,反正那么多山沟,那么多那么高的田埂,还愁没个躲处。再说那么长的“战线”,看园的也就两三个人,而饿肚子的又不仅仅是我们几个,所以玩儿起游击战来,也常常把看园子的大叔大爷们气得够呛。等到成熟下杏的季节,正赶上大人们农田里忙活着锄地,所以下杏的任务又常常离不了我们。这时候是我们最自在最幸福的时候。提着筐子,拿着杆子,到处在园子里出没,哪棵树上的杏大,哪棵树上的杏甜,都了如指掌。要说吃桃吃杏,还是那时候的鲜,小雨刚过,树上红是红的,黄是黄的,金杏又大又软,水杏又嫩又绵,味道不掺一丝隔夜的杂酸,那是在城里永远吃不到的美味。等吃饱了,牙也酸倒了,这时候老师开始定任务,展开比赛,每人下几筐,完成了可以再休息。任务一下,男孩子总是勇往直前,爬上树连摇带打,顿时,树上的杏像猛烈的冰雹一样黄沙沙铺满一地,女孩子和胆小的男孩在地上拾杏。偶尔,树上的毛毛虫掉到谁的头上,也不知道,等到别人提醒,才慌忙放下杏筐,惊慌失措地连蹦带跳,连拍带打,忙活半天,也不知道毛毛虫掉了没有,逗得大家一阵大笑,笑声能在山谷中传来好听的回声。从一下杏儿开始,乡亲们就远远近近开始走亲戚,或提一篮,或挎一兜,给临村没有杏儿的亲戚送去,顺便加深一下亲戚之间的感情。因为桃比杏儿要熟得晚,所以这样的热闹一直能持续到暑假结束。到改革开放后,杏园桃园分到了各家各户,园子比集体时候管护栽培得更好了,只是园子里少了几分过去的笑声和热闹。但代之而来的是乡亲们的脸上浮上了更多的喜悦和笑容。
人是故乡的亲,水是故乡的甜。故乡的井水全是从山里引来。全村分东西两半,各开一口水井。水井全是用山石砌成,方形,有顶棚,旁边还养着几棵茂密的巨柳,像绿衣一样,整个把水井裹在其中。故乡的水特别纯,用现在的字眼儿,叫矿泉水。烧在锅里,见不到城里烧水出现的那种又白又厚的水垢。后来,城市的自来水提醒了乡亲,于是大家就集资,请人在山的高坡上建起了蓄水池,用管子把水引到各家各户,也用上了自来水。有了自来水,人人家里就开始发展起了庭院经济,有种蔬菜的,有种葡萄的,使小小的村庄更加富裕起来。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哪里的黄土都养人。别看故乡偏僻,也别说山多地少,故乡人靠的就是这大山的关照。水从大山来,盖房砌墙的石从山里取,牲畜的草也得到大山里寻。每年农闲时分,乡亲们就把耕牛集中起来放到山里,白天黑夜不回来,让它们在这里饱吃饱喝。您可别担心牛会跑没了,绝对没事,牛的群体意识有时比人都强,再说夏天山上水草丰盛,方圆几百里群山环绕,相当于一个天然牛圈,牛还往哪儿走?等到秋天农忙的时候再把它们赶回来。这中间虽说时间不长,但与赶出去之前相比,那变化实在是大得很,成年牛变得膘肥体壮,油光铮亮,小牛犊一下变成了能劳动的大耕牛。
山村的生活都在山里,吃的是山,喝的是山,消闲的时光也在山里。农闲的时候,乡亲们不是到山里割草,就是进山里割条(编筐用的一种类似柳枝的条子)。到了冬天一下雪,漫山遍野的全是雪花,白的纯洁,白的清爽,小孩子滚雪球、打雪仗,家里坐不住的大人们则上山去打猎,山上有的是野兔野鸡,所以半天下来,总会提回一些下酒的美味。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同样的山,同样的水,在改革开放前,乡亲们的生活不如意啊!猪不让养,口粮不够吃。可如今,故乡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了。仙是什么,龙又是什么?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仙和龙就是党的好政策,有了党的好政策,顺应党的好政策,还有什么山名不了的呢,还有什么水灵不了的呢,还有什么事办不好的呢?大山的水土养育了大山的人,大山的性格养育了乡亲们勤劳朴素的精神。一代代故乡人就在这里繁衍,一茬茬故乡人就在这里耕耘,从没有嫌弃,也从无怨恨,固守着大山,就成了大山的一个部分。这就是故乡的山水,这就是故乡的人文精神。这种自然和人文精神代代相传,成了我基因中的重要内容,无论走到哪里,故乡的山水,总是一道割不断的风景,故乡的乡情总是一种割不断的骨肉亲情。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回眸大山,眼前总涌起一片沉静的波澜;回望故乡,心中总腾起一种无形的力量。
未知的世界,时时都在诱惑着我,但是,我更爱眼前的山,我连梦里都投入大山的怀抱,呼吸大山的气息,攀上大山的肩膀,洞悉山那边的世界。
因为,我是山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