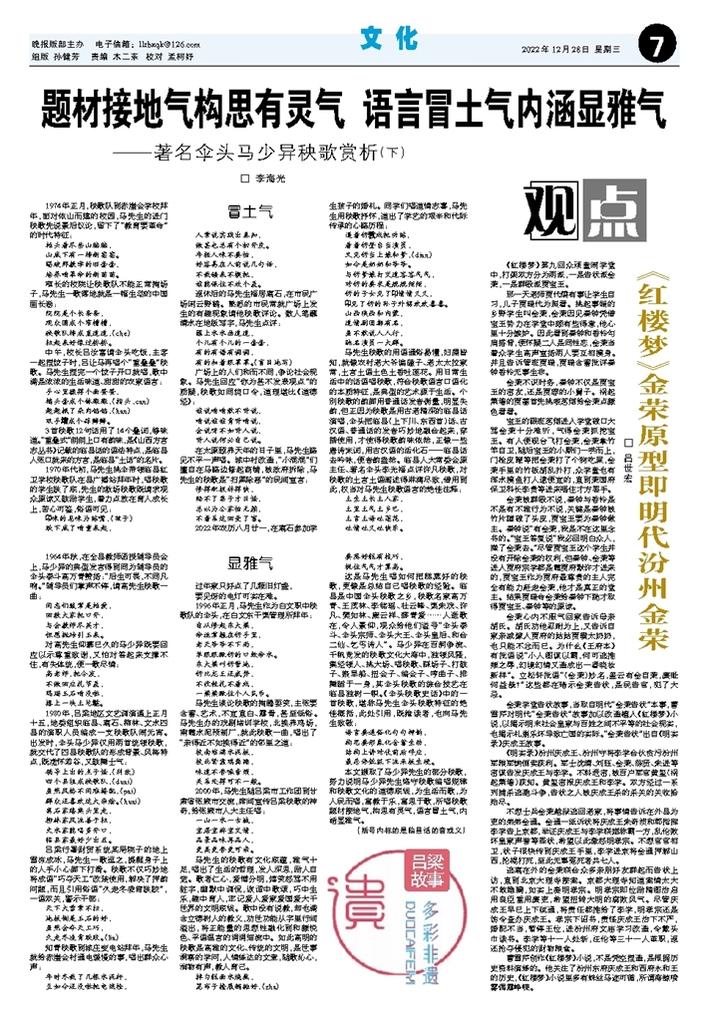□ 李海光
冒土气
1974年正月,秧歌队到赤崖会学校拜年,面对依山而建的校园,马先生的进门秧歌先说景后议论,留下了“教育要革命”的时代特征:
抬头看尽些山脑脑,
山底下有一排新窑窑。
踢破那教学的旧套套,
培养咱革命的新苗苗。
窄长的校院让秧歌队不能正常掏场子,马先生一歌落地就是一幅生动的中国画长卷:
院院是个长条条,
观众围成个窄槽槽,
秧歌队排成直道道,(che)
扭起来好像过桥桥。
中午,校长吕汝富请伞头吃饭,主客一起捏饺子时,吕让马再唱个“重叠叠”秧歌。马先生捏完一个饺子开口就唱,歌中满是浓浓的生活味道、甜甜的农家语言:
手心里揉得个面蛋蛋,
摘头套成个钵璨璨,(指头,can)
匙匙抿了朵肉馅馅,(han)
双手堉成个蒜瓣瓣。
3首秧歌12句话用了14个叠词,够味道。“重叠式”朗朗上口有韵味,是《山西方言志丛书》记载的临县话的语法特点,是临县人张口就来的方言,是临县“土话”的名片。
1970年代初,马先生挑伞带领临县红卫学校秧歌队在县广播站拜年时,唱秧歌的学生跌了底,先生的救场秧歌既请求观众原谅又鼓励学生,着力点放在育人成长上,苦心可鉴,俗语可见:
卬咪的息咪为练嘴,(孩子)
跌下底了咱重来起,
人常说实践出真知,
做甚也总有个初开皮。
年轻人咪不要怕,
好容易在人前说几句话,
不栽锤来不楔把,
谁能保住不放个差。
退休后的马先生福居离石,在市民广场闲云野鹤。熟悉的市民常就广场上发生的有趣现象请他秧歌评论。数人笔蘸清水在地板写字,马先生点评:
蘸上水水画道道,
个儿有个儿的一套套,
有的有谱有调调,
有的扣着眼罩罩。(盲目地写)
广场上的人们和而不同,争论社会现象。马先生回应“你为甚不发表观点”的质疑,秧歌如同绕口令,道理堪比《道德经》:
谁说咱咱敢不听说,
咱说谁谁肯听咱说,
会说呀不如听人说,
听人说何必自己说。
在太原颐养天年的日子里,马先生路见不平一声唱。城中村改造,“小混混”们擅自在马路边修起商铺,被政府拆除,马先生的秧歌是“扫黑除恶”的民间宣言:
修得积极拆得快,
赔不了票子才日怪,
总以为公家怕无赖,
不着系这回受了害。
2022年农历八月廿一,在离石参加学生孩子的婚礼。同学们唱道情志喜,马先生用秧歌抒怀,道出了学艺的艰辛和代际传承的心路历程:
逼着伢敩戏把功练,
看着伢登台当演员,
又见伢当上娘和爹,(dian)
如今是奶奶和爷爷。
与伢爹娘打交道客客气气,
对伢的要求是规规矩矩,
伢的子女见了卬情情义义,
卬见了伢的孙子外甥欢欢喜喜。
山西陕西和内蒙,
道情剧团都有名,
虽不敢说人人行,
驰名演员一大群。
马先生秧歌的用语通俗易懂,妇孺皆知,就像农村老大爷谝磕子、老太太拉家常,土言土语土色土香吐莲花。用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唱秧歌,符合秧歌语言口语化的本质特征,是典型的艺术源于生活。个别秧歌的韵脚用普通话发音衡量,明显失韵,但正因为秧歌是用古老精深的临县话演唱,伞头把临县(上下川、东西首)话、古汉语、普通话的发音巧妙地融合起来,穿插使用,才使得秧歌韵味依然,正像一些唐诗宋词,用古汉语的活化石——临县话去吟咏,便音韵盎然。临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著名伞头李光福点评许凡秧歌,对秧歌的土言土语阐述得淋漓尽致,借用到此,权当对马先生秧歌语言的绝佳注释:
土生土长土人家,
土里土气土乡巴,
土言土语吐莲花,
吐情吐义吐快乐。
显雅气
1964年秋,在全县教师函授辅导员会上,马少异的典型发言得到同为辅导员的伞头泰斗高万青赞扬:“后生可畏,不同凡响。”辅导员们掌声不停,请高先生秧歌一曲:
同志们鼓掌是抬爱,
回敬大家把口开,
与会教师尽英才,
但愿抛砖引玉来。
对高先生仰慕已久的马少异既要回应以示尊重致谢,又怕对答起来支撑不住,有失体统,便一歌尽情:
高老师,把令发,
不做回应礼节差,
玛瑙玉石咱没啦,
撂上一块土圪垯。
1980年,吕梁地区文艺调演遇上正月十五,地委组织临县、离石、柳林、文水四县的演职人员编成一支秧歌队闹元宵。出发时,伞头马少异仅用两首统领秧歌,就交代了四县秧歌队的形成背景、风格特点,既虚怀若谷,又鼓舞士气:
领导上出的点子怪,(别致)
四个县组成秧歌队,(duai)
虽然风格不同难搭配,(pai)
群众还喜欢这大杂烩。(huai)
离石家路熟头里走,
柳林家风流善于扭,
文水家能唱多开口,
临县家最好少出丑。
吕梁行署财贸系统某局院子的地上雪冻成冰,马先生一歌逗之,提醒身子上的人手小心脚下打滑。秧歌不仅巧妙地将成语“巧夺天工”改装使用,解决了押韵问题,而且引用俗语“久走冬凌肯跌跤”,一语双关,警示干部:
天下大雪常不扫,
地板倒是玉石的好,
虽然会夺天工巧,
久走冬凌肯跌跤。(lia)
知青秧歌到城庄变电站拜年,马先生就给赤崖会村通电缓慢的事,唱出群众心声:
年时冬栽了几根水泥杆,
至如今还没啦把电线拴,
过年家只好点了几颗旧灯盏,
要见伢的电灯可实在难。
1996年正月,马先生作为白文职中秧歌队的伞头,在白文东干渠管理所拜年:
自从修起东大渠,
命运掌握在伢手里,
老天爷爷不下雨,
单眼眼瞅伢的口救命水。
东大渠叫伢管地,
伢比龙王还威势,
不收牲礼不看戏,
一梁梁瞅住个人民币。
马先生谈论秧歌的掏腾耍笑,主张要含蓄、艺术,不宜直白、露骨,甚至低俗。马先生办的戏剧培训学校,北挨养鸡场,南靠水泥预制厂,就此秧歌一曲,唱出了“亲得近不如挨得近”的邻里之道:
校南堆满水泥板,
校北紧靠鸡粪滩,
味道不香噪音烦,
关系处得可不一般。
2000年,马先生随吕梁市工作团到甘肃省张掖市交流,席间宣传吕梁秧歌的神奇,给张掖市人大主任唱:
一山一水一古城,
宜居宜游宜交情,
品景品味再品人,
更美更香更可亲。
马先生的秧歌有文化底蕴,雅气十足,唱出了生活的哲理,发人深思,励人自觉。歌者仁心,爱憎分明,嬉笑怒骂不用脏字,幽默中调侃,诙谐中歌颂,巧中生乐,趣中育人,牢记爱人爱家爱国爱大千世界的文明底线。歌中没有说教,却也满含立德树人的教义,劝世功能从字里行间溢出,将正能量的思想性融化到和颜悦色、平语温言的涓涓细流中。如此高明的秧歌是高雅的文化、传统的文明,是世事洞察的学问,人情练达的文章,随歌沁心,润物有声,教人育己。
拌匀糕面水烧熬,
笼布子揸展铺摊好,(zha)
要蒸好糕有技巧,
捉住气气才算高。
这是马先生唱如何把糕蒸好的秧歌,更像是总结自己唱秧歌的经验。临县是中国伞头秧歌之乡,秧歌名家高万青、王茂林、李铭瑶、杜云峰、渠朱戏、许凡、樊如林、康云祥、薛青爱……人逝歌在,令人景仰,观众给他们谥号“伞头泰斗、伞头宗师、伞头大王、伞头皇后、和合二仙、乞丐诗人”。马少异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秧歌文化大海中,独领风骚,集经领人、挑大场、唱秧歌、踩场子、打鼓子、搬旱船、扭会子、编会子、哼曲子、排舞蹈于一身,其伞头秧歌的综合技艺在临县独树一帜。《伞头秧歌史话》中的一首秧歌,堪称马先生伞头秧歌特征的绝佳概括,此处引用,既飨读者,也向马先生致敬:
语言要通俗化句句押韵,
构思要形象化含蓄生动,
结构上讲对仗前后呼应,
最忌讳低级下流呆板生硬。
本文撷取了马少异先生的部分秧歌,努力说明马少异先生恪守秧歌编唱规律和秧歌文化的道德底线,为生活而歌,为人民而唱,寓教于乐,寓思于歌,所唱秧歌题材接地气,构思有灵气,语言冒土气,内涵显雅气。
(括号内标的是临县话的音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