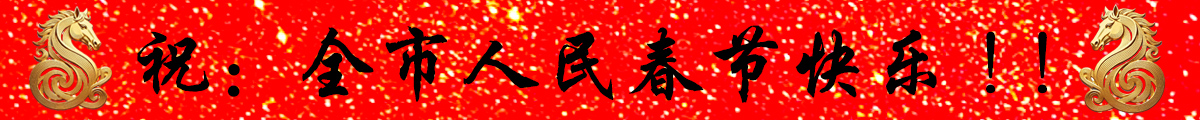学诗渐悟(下)
□ 李 峰
编者按:李峰先生《学诗渐悟》一文,凡六千余言,本栏分为上下两期刊出。《学诗渐悟(上)》刊于本报1月23日。
诗到语言为止
对于写诗多年的人来讲,道理深刻。在写诗实践中,一开始,大部分习诗者,都是先寻找诗情诗意,甚至是一个重大的主题。比如对山水的抒情,对爱情的憧憬,对故乡的回忆等等。这些作品更大一部分,应该算是习作、练笔。写着写着,速度就会由快变慢,很多自己写的诗歌,同质化倾向会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脑子一片空洞,什么也写不出来的情况。好多诗歌爱好者,就是在这个时候,真正体会到了诗歌的难写,写诗的深奥。倘若没有导师的引导和强大的悟性,很有可能就放弃了诗歌,停下了手中的笔,殊为可惜。也有一些探索者,执着地攀登,企图在冰山上找到那个诗歌的“雪莲”。
诗的语言是最重要的,看一段分行的文字,是不是诗,关键是看语言,是不是诗歌的语言。我个人认为,语言比题材更重要。强硬地讲,生活中或想象中,什么都可以写成诗,并没有什么巨大和细小题材之分,关键是看你写出来的文本,是不是运用的诗歌语言。否则,再重大的题材,再有诗意的主题,写出来的也不是诗。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有成就的诗人,一生能不断地写下去的“奥秘”。否则,哪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写成诗。
诗写到“随心所欲”应该就算作熟练了。在这个状态里,素材、题材信手拈来,在随便一样普通不过的事物中,都能迅速找到诗意,找到可以凝练成诗的核心东西;在一点一点朦胧的诗意的素材中,准确地寻找到一个切入点,而这个切入点是具有共同感受特质,又独具新意和慧眼的导入处。它不是神经质的胡乱臆想,而是建立在人类共同感知感受基础上的创新,也所谓有新意、立意新;找到这个切入点后,能从四面八方,调集想像、经验、关联物、现实等,熟练构架诗歌的形态,使一首诗中,有疏有密、有远有近、有具象有抽象、有铺叙有抒情、有哲理有事物。仔细端详中,有骨有肉、有平面有立体、有似曾相识有顿然开朗的特征。这不是简单的素材的堆砌,也不是有一两句饱含哲理的东西存在,而是用五个指头,一把能抓起来的一个分行的整体。这样的诗歌,每一句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虽然有的诗句表面看起来不关联,那是一种深入的诗歌跳跃,不是废话,需要有一定的阅读经验,方能读懂。要达到写诗的“随心所欲”,非一日之功。如同习练书法,必须经过读帖临帖的漫长的过程,必须经过苦心练笔结构书法的过程,必须经过深入理解汉字之美的过程,然后,才能写的得心应手,如行云流水。
把诗写“拙”
写诗有技巧,此话一点都不假,但是,诗歌最美的境界或最大的技巧,是把诗写“拙”了。这个道理,如同比喻聪明人“大智若愚”。
好的诗歌,不是靠一些形容词或华丽词藻堆砌而成,相反,这些东西,都是新诗的大敌、大忌。娓娓道来的东西不见得比隆隆震耳发聩的分量轻;从细小处切入的不见得比一开头就高呼口号的效果差;朴实的轻缓的叙说不见得比迫击炮一样发出的火力小。书法中有一种书法叫“丑书”,尽管现在书法界还在大加议论,但我总认为,这种书法也不失为一种状态,这是一种书法的大美。我们常说的大美至简,在丑书里也有体现。写诗是一种特殊的创造,特殊的艺术劳动,整个过程,需要的是一种灵感的推动。一开始写诗时,每个人都是在找到一个鲜明的主题后,便开始酝酿,同时,也在寻找一些抒情的词语,这些词语大多都在他的阅读范围内,都是一些经验性的惯用的词语。
比如,用月亮比喻爱情,用醉酒表示消愁,用乌云暗示坏心情等等。这样的诗歌,表现出来的都是声嘶力竭、悲悲戚戚,仿佛在展现一些通用品似的词语,表达的也是一种共性的感情和感觉,都是一种小我的情愫,只能孤芳自赏,内行人读后索然无味,如一具僵尸。艺术的东西要靠打败自我、冲破规矩、穿透平庸,才能有独立风骨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情,平淡中暗藏深刻的东西,才会有诱人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对于写诗的人来说,这需要一个艰难的跨越和对自我的彻底否定。在这一点上,我又不承认天才,比如儿童画,幼年时的孩子,天真无邪,一些画画的大胆超凡,想像会让成人难以想到。但这些孩子长大后,再画,一定不会再有那种儿童作品,也不可能有那些奇特的想像。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一些约定俗成的樊篱中。走出来的就是艺术家,留在里面的就是匠人。再说写诗,诗是艺术的语言,而被语言牵制牵着走的诗人,一生写的诗都是一个调调,寡味。反过来,人牵着语言走,甚至语言融化在诗歌里,写出的诗才是好诗。好诗,拙中自有大乾坤。
诗的“不知所云”
诗歌的所谓“不知所云”,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写诗的人,诗学基础不扎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后,那些抒情都声嘶力竭了,那些大词都用完了,那些主题都写遍了,再也写不出诗来了。然后,开始寻求新的路径。这其中,有的诗人,就开始大量地读中外著名诗人的作品,对照自己的作品,找寻差距,并对诗学理论进行研究探讨,尝试着新的创作方法。尽管这种探求很艰难,但他们很用功,很专注。这时,悟性好的一些诗人,就会脱颖而出,就会在创作上出现爆发,就会豁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创作境界而一发不可收,步入写诗的井喷状态。悟性差一些的诗人,就开始灰心丧气,甚至不再写诗。即便继续坚持写诗的,进步也很慢很小。这样的诗人里,不可能产生重要的诗人或大诗人。而这时的创作阶段,他们的作品往往是与以往的诗歌出现决裂,甚至判若两人,面目全非。对于阅读者来说,这些作品已突破惯性的思维,需要重新开启一种诗歌的心智阅读,需要一种固定思维的穿越。因此,很多诗歌作品初读起来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多读几遍,深入进去,慢慢也就体会清了。这是一种思维、音像、语言的陌生,属于诗歌的特性,没必要大惊小怪和指责。
但另一种情况就有别了,有的诗人不去沉下心来,深入研读中外名诗和诗学理论,或研究时浅尝辄止,没有学到根本。但他们又怕别人批评他们的作品幼稚、平庸,于是,就开始玩假深沉、玩云山雾罩、玩文字游戏。这样的作品写出来,当然就是很肤浅很寡淡的一个花架子,我认为这是在糟蹋诗歌。这样的不知所云,写诗的人不懂,看诗的人也不懂,导致了一些人对新诗的责骂和误解。
诗的“路子”
诗歌写到一定的水准时,才配谈走什么样的路子。如同习书作画,先把基础打好,比如临帖、结构、用墨、造型、素描、速写、解剖等等,这都是规定的动作,有些甚至是终身需要锤炼,反复研习的东西。写诗也一样,首先是爱诗,不停地读,不断地看,练出一双火眼金睛,一首诗拿到手里,大致一看就能看出是不是一首好诗。
我有一个文件盒,就是把一些网上或微信上看到的好诗,打印出来,存放在文件盒里,并在盒子封面上标明《我喜爱的诗歌》。闲暇时,拿出几首来反复品味,细读,总有一些启发和收获。当然,喜爱不喜爱的标准,是我对诗歌个人的理解和评判。这些诗中有名家大家的,也有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作品。也有一些收藏了的诗歌,过一段读时,已感到有一些问题了,便从这个盒子里剔出去。这样,在大量的阅读中,慢慢地就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一个认知标准。
其次是要不断地写,没有量就没有质。当然,这些书写不是简单地机械地进行同质化的写作。每次写作,都是对生命、生活、人生本质的一次感悟,而不是停留在一些惯性思维中的一般认知。长期以往的品读,方能真正领略到好诗的美妙,才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诗歌是个什么样子,也才能廓清写诗的思路,从而,渐渐地形成独特的属于自己的诗歌风格和道路。而每个诗人诗风的形成,背后一定有一种理念和理论在支撑,这些东西是属于灵魂性的,伴随着诗人诗风的稳定,根深蒂固。这样的诗人,也才能算是有自己独立诗歌道路的诗人。
所谓“知识性写作”与“民间性写作”,只是诗歌评论家眼中的两个概念。如同艺术中的学院派与乡土派。在诗歌的实践中,它们并不是截然无关的,更不是对立的。相反,它们是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存在的。民间性的写作也离不开知识,知识性的写作也不是无中生有。这两种写作形态中,都有非常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如藏棣、欧阳江河,如韩东、于坚。需要警惕的是这两种写作形态中的诗歌文本的极端性。不要把知识性写作等同于知识分子写作,那就是诗人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封闭起来了,让诗歌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失去了应有的温度。
事实上,在大量的诗歌实践中,没有绝对的“职业诗人”。因为诗人不是制造诗歌分行文本的机器,而是一些具有对生活、自然、社会有独特认知和抒写能力的人。他们把生命融入诗歌语言中,从而才有精彩的诗歌文本。民间性的写作,也不是要把诗歌写成“口水诗”,那是对民间性的曲解,对诗歌的不敬。民间性是诗歌中的人性,它有人性自带的光芒。表现在诗歌文本上,它体现的是一种纯粹、干净和温暖,而不是一些简单分行的语言,更不是词语的垃圾。吸取精华,才能使诗歌更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