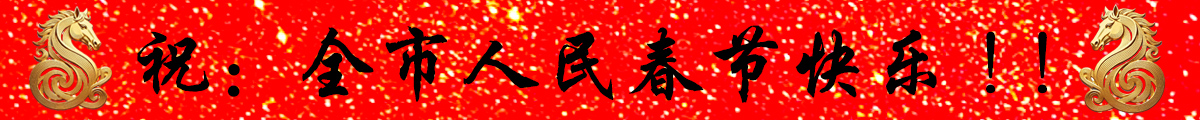鳜鱼肥
□ 钱续坤
生在江南水乡,童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捕鱼捞虾了;捕捞的方法多种多样,用钩钓、用网兜、用叉戳、用手摸等等,皆能满载而归。不过也有令人棘手的鱼儿,一是黄丫,二是鳜鱼,因为黄丫的鳍尖锐无比,鳜鱼不但牙齿锋利而且背上长满倒刺,一不小心,会常常痛得我们龇牙咧嘴,叫苦不迭。因此捕捞到这两种鱼儿,多数孩子宁可不要也不愿去沾惹它;而我却如获至宝,因为所有的鱼儿都是我垂涎的对象。
说来惭愧,有很多年,我一直将“鳜鱼”写作“桂鱼”,及至后来读了张志和的诗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这才知道浑身缀满斑点、样子极为难看的鳜鱼,竟然在唐宋之后就成了文人墨客的最爱。当然,这“最爱”是颇有讲究也值得回味的:首先,就是它的肥美。吃鳜鱼最好的季节是初春和深秋,古诗上早就有“昨夜江南春雨足,桃花瘦了鳜鱼肥”和“野阔江寒一雁飞,碧芦花老鳜鱼肥”的说法;有美食家之称的汪曾祺先生,对其味道更是赞不绝口:“鱼里头,最好吃的,我以为是鳜鱼。”“鳜鱼刺少、肉厚。蒜瓣肉。肉细、软、鲜。清蒸、干烧、糖醋、作松鼠鱼,皆妙。氽汤,汤白如牛乳,浓而不腻,远胜鸡汤鸭汤。”其次,就是它的寓意。“鳜”与“贵”谐音,“鱼”与“余”谐音,象征“富贵有余”,这也难怪其貌不扬的鳜鱼,会成为齐白石、李苦禅、潘天寿、王雪涛、高冠华等丹青妙手的心仪之物。
我的母亲是勤劳朴实的农家妇女,她对烹饪技艺没有半点研究,不过总是变着法子将鱼烧得有滋有味,这在童年时代可谓是莫大的享受。而在烧鳜鱼时,她始终都是一种做法,那就是清蒸。清蒸其实很简单,母亲先将新鲜的鳜鱼除去鳞鳃和内脏,洗净放入盘内,然后用精盐在鱼身上均匀擦摸一遍,大约腌渍一刻钟之后,再用水冲洗一次;此时的我,早已在灶底将火烧得旺旺的,母亲则不慌不忙地在鱼身两侧划上十字刀花,紧接着将鳜鱼平放到瓷盘内,上面洒点葱段、姜片、精盐和食油,便算大功告成了;剩下的最后一道工序,则是入锅旺火清蒸。要不了十分钟,我家那原本低矮的厨房便香气四溢了,而围在灶边的我们弟兄三人更是口舌生津。蒸熟的鱼肉嫩鲜爽滑,清醇味美,用筷子轻轻一搛,一块一块的,如剥好的蒜瓣;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们不会这样细嚼慢品的,用狼吞虎咽来形容最是恰当不过,有时甚至真的连鱼汤都舍不得放过。
工作之后,出入宾馆饭店的机会较多,这使我品尝过不少以鳜鱼为主料的菜肴,如“糖醋鳜鱼”“松鼠鳜鱼”“柴把鳜鱼”“八宝鳜鱼”“网油鳜鱼”“茨菰鳜鱼”等等,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徽州臭鳜”。之所以印象深刻,倒不是因为两百多年前那个美丽的传说,主要是在我以前根本不敢接触酸甜苦辣咸五味之外的第六味——臭味了。有一次在皖南的绩溪县勉为其难夹尝了一筷子,结果爱不释“口”,那种臭中带香带鲜的感觉,在整个口腔内飘荡,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这与母亲在我童年时所烧的“清蒸鳜鱼”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古诗云:“明日主人酬一座,小船旋网鳜鱼肥。”在这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如果有人发出这样盛情的宴请,谁不愿意去?反正我是顾不上斯文,早就趋之若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