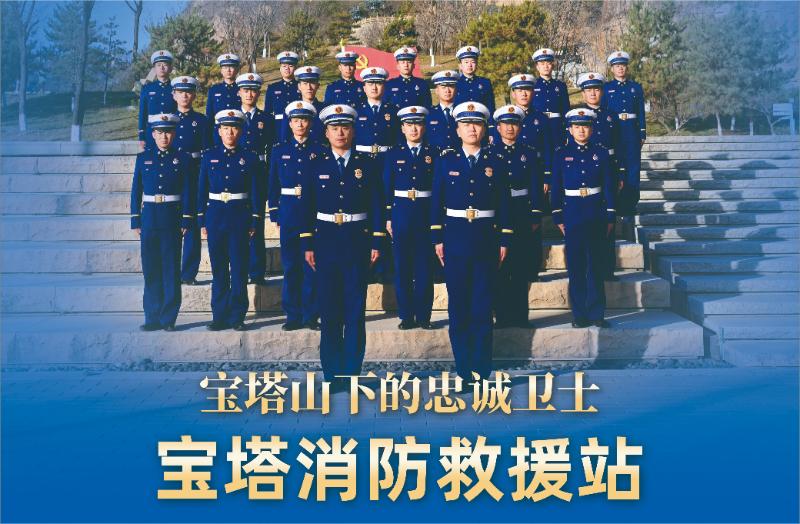祭 糕
□ 雒小平
在我们乡下,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总爱把枣糕称为“祭糕”。这看似不经意的称谓,其实是很有些说道的。
在农村长大的人,都知道“软糜子蒸不出硬糕”这句俗语,但很少有人知道糜子的书名叫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糜子曾是北方山区广为种植的一种粮食作物,“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至少在四五千年以前,糜子就已被先民驯化,堪称我国最古老的农作物。毋庸置疑,人类在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的历史进程中,糜子可谓功不可没。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追宗祭祖的传统。为了感恩祖先的功德,先民们就用收获的果实作为祭品,因此,糜子应运而有了祭祀的功能。商周时期,黍米也被蒸熟和牛羊等牺牲一起进行祭祀,这便是“祭糕”的雏形了。大约到了唐宋时期,祭糕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成熟的祭品了。后来,随着祭祀完毕,牺牲、腊肉和祭糕等被分给乡民食用,祭糕的做法也被传入民间,并相沿成俗成为一种民俗食物。
显而易见,吃祭糕的民俗在我国已有很久的历史了。到我懂事时,已经看不出祭糕的祭祀功能,但因其具有特殊的意义深受民间推崇。比方说,过年要吃年糕,酬谢乡邻,招待亲戚,家家都要碾一面囤的糕面;做事宴要吃糕,大点的事宴则需几斗米的糕面,庄户人家往往得用几年的时间积攒;婴儿满月、过晬,孩子们过生日、考学,当然更离不开吃糕了。糕谐音为“高”,寄寓着健康成长、金榜题名,生活越过越好,意义非同小可,尽管当时生活艰难,但再穷的人家,也要千方百计让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吃一顿糕。
记忆中,我每逢过生日,母亲都会早早地起床,搂柴,捣炭,生火,坐锅,添水,舀面……一阵忙碌之后,闻得水锅沸响,母亲便将夹箅放入锅中,铺好笼布,在蒸腾的水汽中,将拌好的糕面一层层撒进锅里,一边冒着热气把煮熟的红枣均匀地点在其中。“一层糕一层枣把它蒸出,俗话说叫圪哒祭糕片子”,有秧歌形象地道出了蒸糕的方法。不一会儿工夫,只听母亲喊一声“熟”,便呼地将糕端出铁锅,熟练地反扣到案板上,然后揭去夹箅笼布,就着热气用双手将糕垛拍得啪啪响——浓郁的糕香便弥漫了开来。
如果遇上丰年,还可以吃上油糕。油糕与枣糕相比,味道更香,更坚韧,口感更好,更令人垂涎三尺。枣糕蒸熟了即可食用,有道是“省油吃素糕”,而油糕还需经过搋(音chuai)糕、捏糕和油炸等工序。不消说,搋糕最为重要。记得糕出锅后,母亲将袖管高高挽起,一边蘸着凉水,一边哈着热气,将糕团在案板上揉来搋去,待到糕团搋好,母亲已是汗流津津、气喘吁吁了。近年来饭店的油糕之所以饱受诟病,其原因就在于少了搋糕的工序所致。
五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有印象,吃枣糕还有一条禁忌,就是在开吃前,大人们总忘不了先切下一片,庄重地贴到糕垛背后,然后对猴急的孩子们正色训诫:第一口轮不上人吃!那么,这个神秘的细节到底包含着怎样的信息?今天看来,兴许与古代的祭祀有关呢!我想如果这样理解,那就顺理成章了。但有人认为可能是蒙元统治时流传下来的遗俗,我总觉得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星移斗转,社会巨变。随着高产作物的引进、推广和人口的增加,以及传统饮食结构的嬗变,特别是近年来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镇,等等原因,糜子已经逐渐退出了主粮的地位,如今回到乡下,也很难再看到过去秋风乍起、糜子迎风摇曳的动人景象了。同时,由于生日、年节、婚宴等宴席大都改到酒店举行,过去一统天下的糕菜,也势不可当地被丰富多“菜”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套餐所取代。糕,曾作为多少代人的最爱,似乎只留下了一个象征性符号。
其实,令人忧虑的远远不止于此。试问一下,今天我们还有多少人知道“祭糕”的称谓,知道“祭糕”的来历?再简单一点,年轻一代当中,还有多少人会蒸糕,掌握蒸糕的技术?尤其是寄托着厚望的孩子们,还有多少人认识糜子,知道糜子是蒸糕的原料呢……
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如果事宴是在农村举行的,汤菜油糕、枣糕(祭糕)仍然是不少人家的首选。许多在饭店摆的酒席,油糕或枣糕(祭糕)依然是一道不可或缺的主食。还有,在一些城市,枣糕已变身为一种地方风味小吃,仍然受到不少人的青睐。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种起源于祭祀祖先、浸润先民情感的食物,依然有着独特的魅力,说明经过岁月淬炼、根植于民族骨髓的民俗文化,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滚糕——”浑厚的叫卖声在街头响起,穿过喧闹的市井敲击着我的耳鼓,我猛然意识到:糕,中华民族最悠久的食物之一,它有如黄金般耀眼、醇酒般绵香和坚韧耐饥、久食不腻的特质,使它历久弥香、绵延不绝,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记忆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我们绝不可仅仅陶醉于风味小吃的满足之中,而应该堂皇地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因为,我们只有记住了“祭糕”,才不会忘记祖先,不会忘记历史,心中才会激荡起民族的自豪,才能永远记住乡愁和握住爱我家乡、爱我中华的精神密码。这样,来自街头的那一声悠长的叫卖,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