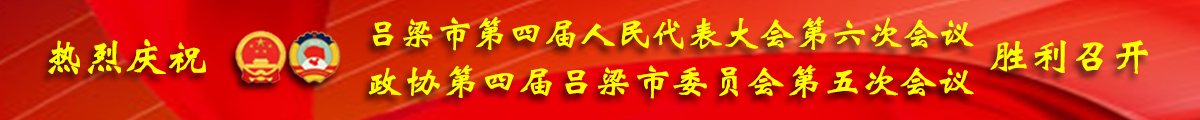人间值得
□ 李峰
“人间值得”这四个字,足够珍惜、珍藏一生了。
我是去年在一辆出租车上,看到这四个字的。那是一个秋日,我坐在出租车的后排,偶然间,看到后视镜上,挂着一个红色的吊牌,长方形的,上面写着“人间值得”。开车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看样子,很沉稳,也很本分。之前,很多的出租车上,也都挂着这种吊牌,有的是挂着一个葫芦,有的挂着“恭喜发财”,有的挂着观音菩萨,也有的挂着一个“忍”字。我想,挂什么吊牌,一定与司机的喜好,或信仰有关,也一定与司机的修养相关。挂“人间值得”吊牌的,肯定是他喜欢这四个字,他珍惜这四个字的分量,或者说,他热爱这个人间,热爱生命、生活。那天,我坐在后排,用手机,把这个吊牌,拍了下来。那时,我在想,一个出租车司机,整天风里来雨里去,起早摸黑,拼命拉客。遇到运气好时,一天下来,赚个三五百元,赶上运气不佳时,耗上一天,也指不定能赚几两碎银,说不准,还不够交份子钱。但,就是这样的日子,他也坚信:人间值得。这就是活着的定力,活着的滋味。我很敬佩那个出租司机,也很敬重那四个字。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日子里,闭着眼睛一想,那些人间中的风风雨雨、宦海沉浮、恩恩怨怨,都过去了。所有的人间疼痛,也都过去了。有人说:“感谢生活。”我说:“感谢人间,感谢在人间的这一遭。人间真的值得。”
尘世中的一切都安静下来后,我喜欢一个人,独坐在窗前,看窗外月季花的绿叶、花朵,还有那些星星点点的刺,一片叶子黄了,一朵花枯萎了,慢慢地落在地上,那么安然、安逸;也喜欢一个人,在一条小径上散步,不看小径之外的高楼不听汽车的鸣笛,只在乎小径的清爽与宁静。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最适合回忆,最适合品味。无所谓主题,无所谓对错,也不再分轻重缓急。此时,我就像一根随风摆动的柳条,一池春水中游来游去的一只野鸭。或者是,在一个黄昏,独自坐在树林中一只条椅上的一个老者。落日中,正陷入散漫的回忆。
一只小麻雀,落在一棵银杏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多好听呀。六十多年间,都在为生计、功名奔波,已厌倦了那些轰轰烈烈,跌宕起伏。此时的我,只要一眯起眼,就会想到,年少时,我们兄弟三人,睡在一条土炕上,整夜关注孵小鸡的情景。那时,我们住在汾阳县城指挥街13号的一个大杂院中,大院北面是五间窑洞,中间三间归原房主,两边各一间为房管会的,分配给我们家居住。父母住西边一间,我们住东边一间。那一年,我们家喂的一只老母鸡,开始孵小鸡。父亲怕院子里的其他鸡,糟蹋老母鸡肚底孵的那些鸡蛋,便找来一只柳编的筐子,并在筐子底,铺了一层麦秸,然后,把鸡蛋一颗一颗摆了进去。最后,再把老母鸡放进去。用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一间产房。这个孵鸡的筐子,父亲就放在我们住的那间窑洞里。这样,既安全又凉快。白天有时候,老母鸡就跳出筐子,到院子里找食吃,不过,时分不大,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还是跳进筐子里孵小鸡。这个筐子的位置,离我们睡觉的土炕很近。夜里,熄灯后,我们弟兄三个,就爬在枕头上,看一会孵小鸡。一边看一边掰着指头,数小鸡孵出的时间。有一天傍晚,父亲告我们说,那些小鸡今夜就要破壳出来了。我们三个听了很兴奋。那一夜我们就都爬在枕头上,谁也不肯睡去,三双眼,都在盯着筐子里的动静。果然,到后半夜,老母鸡肚底的那些鸡蛋,就有小鸡一个个破壳而出,毛绒绒的,个个都很可爱。那一夜,我们弟兄三个,都没睡。直到天亮后,才跑到西边的窑洞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想想,那个时候,我们弟兄三个,是多么的亲热、亲近。那一条土炕上,不知留下了我们多少美好的夜晚。在父母眼里,我们又何尝不是三个很可爱的小雏鸡呢。之后的岁月里,我们都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日子中,总是离多聚少。一晃已一个甲子过去了,多么留恋那窑洞、那土炕、那些夜晚。尤其是父母走了之后,从血缘关系上讲,兄弟就是最亲近的人了,真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关系。这份兄弟情,是值得一生珍惜的,那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是一脉相承的血缘。
算起来,大学毕业已经41年了。这么些年里,每次聚会,同学们都会回忆起当年在一起学习、生活的一些事情,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次分别,都是依依不舍。1980年,我才17岁,就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来到太原求学。说实在的,我很知足。原因之一,就是我考进了我喜欢的专业——文学。仔细回想一下,如果我当时,插了队,顶替上了班,或者考到别的专业,我的人生之路,就又是另一个版本。我发表的第一篇散文《甜苣》,就是在写作老师孙秀乾先生的指导下,发表在《大学中文刊授》上的。那是一个很薄的册子,但,很正规,还有书号,这篇散文,应该算我的散文处女作,我把它收在了散文集《白菜花》中。也就是从大学时期,我就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一走,就是40多年。孙秀乾先生还为我起了个笔名“河清”,并注明意为“黄河清,圣人出”。多年间,我断断续续用过一些。能看得出孙先生对我的期望与鼓励。毫无疑问,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把我培养成了一个作家。我为我的选择骄傲,此生值了。记得,读中文系期间,我与几个文学爱好者,在家乡,办起了春笋文学社,油印了《春笋》刊物,封面是我在刻蜡版纸上画的,画面是一个大春笋,寓意着我们的文学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的文学梦,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大学里,我还加入了春禽文学社,并积极撰写稿件,帮助油印《春禽》刊物。想想,那真是一个文学家的梦想天堂,一个梦想起飞的地方。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大学毕业前,我就写出了《谈谈微型小说的写作》,被《中小学生拼音报》连载,并完成了毕业论文《比较〈金钱〉和〈子夜〉的结构与人物塑造》,刊登在《山西文化》上。那个年代,我的空气中,无时无刻都弥漫着文学的味道。还有我的诗歌老师马作楫先生,多少年间,我们亦师亦友,书信之间,谈诗歌、谈人生、谈处世。我24岁,出版第一本诗集《青春的折光》时,马作楫先生还为我写了序言《执着的追求》。他写道:“这是一片桃李情染绿了的诗心在跳动,也是对诗爱的真诚的心在心心呼应。”就是这桃李情,不仅染绿了诗心,更染绿了我们的师生情。之后的日子里,我多次去山大拜访马作楫先生。我把他送我的《马作楫文集》摆在书柜里,把与他的合影,珍藏在影集中。那些书、那些照片里,都写满了:人间值得。
从人生历程上来看,我算是很幸运的一个人。念大学,上了自己喜欢的中文专业。毕业之后的工作,又大部分都与文学、文字有关。最早在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宣传部工作,调回县城后,便从事秘书职业。之后,一直在广播电视部门,担任领导干部,直到退休。回过头来看,有些事是很蹊跷的,仿佛是命中注定,又像是一种缘分。我一参加工作,在汾酒厂宣传部,结果退休时还是在市委宣传部;离开汾酒厂时,我是广播电视站站长,回到县城后,在广电领域领导岗位一干就是二十四年,退休前还兼任着汾阳广播电视台台长;在汾酒厂我拿到了《山西教育报》的第一个记者证,退休时,我交回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期间,取得了记者的中级职称,并被授予“新闻采编专家”称号。这些好像都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我来说,一生喜欢文学,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写过材料,当过秘书,搞过新闻,从事过宣传工作,而且,一辈子与文学不离不弃,写作、发表、著书立说,存留后世,值了。
事业和爱情,是人生两件重要的事情。我与爱人最早相识,也是因为文学。上大学读中文系时,我们几个同学,组织起了春笋文学社,办起了《春笋》油印刊物。那个年代,没有激光照排,也没有电脑打印,文学社的成员写好作品后,就要找熟人打印。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春种秋收》,放假后,就回老家找人打印。那时,年轻认识人少,更不知道谁家有打印机。我的三姑就帮我找到了县政府办公室的同学,她是打字员。她接下我的手稿后,便应了下来,答应不忙时,帮我打。没几日,我的那个小说就打印好了,我校对后,便正式印了出来。之后,就和其他文学社成员的稿子,装订成册,便产生了第一期《春笋》。又一个假期到了,为了表示对打字员的感谢,我买了一个玻璃小杯,送给了县政府办公室帮我打印小说的打字员。她就是后来我的结发妻子,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应该说,是文学牵起了我俩的姻缘,让我们相爱终生。结婚后,回忆起当时的相识,她告诉我,那个水杯她一直珍藏着,放在她们家窑洞的壁柜里。我的那本《春笋》油印刊物,也一直保存着,放在我的书柜中。什么是缘分,这就是,值得一生珍藏。
没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我也是。仕途上,我在而立之年,被任命为汾阳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不惑之年,主阵汾阳广电。从副局长到一把手,在汾阳广电一干就是24年。2010年至2017年,还兼任中共汾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这个连芝麻官也不算的“小吏”,给了我一次施展领导才能的机会。也就是相当于,我在汾阳广电做了14年“将军”。说真的,我当得很难,但又当得很值,很快乐。难是难在这个摊子,缺钱、缺人、人事关系复杂;值是我在任期间,彻底重塑了汾阳广电的形象。14年中,汾阳广电资产不断壮大,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好作品频频获奖,文明建设从县级文明单位,一路攀升至山西省文明单位。可谓是一路艰辛一路歌。那些年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别人称呼你个什么长,而是我的价值能变成干部群众的口碑,我的爱好特长能变成工作的本领。在人的一生当中,什么是幸福,能把个人的智慧变成社会实践的行动,能把自己的爱好与工作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幸福,再苦再累也是快乐的。当官不在大小,不在长短,做点事,做好一点事,就好。此生值了。
人间值得的事太多了。在这条漫漫的人生路上,无论荣华富贵还是苦难重重,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是我们活过的生活,都值得珍惜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