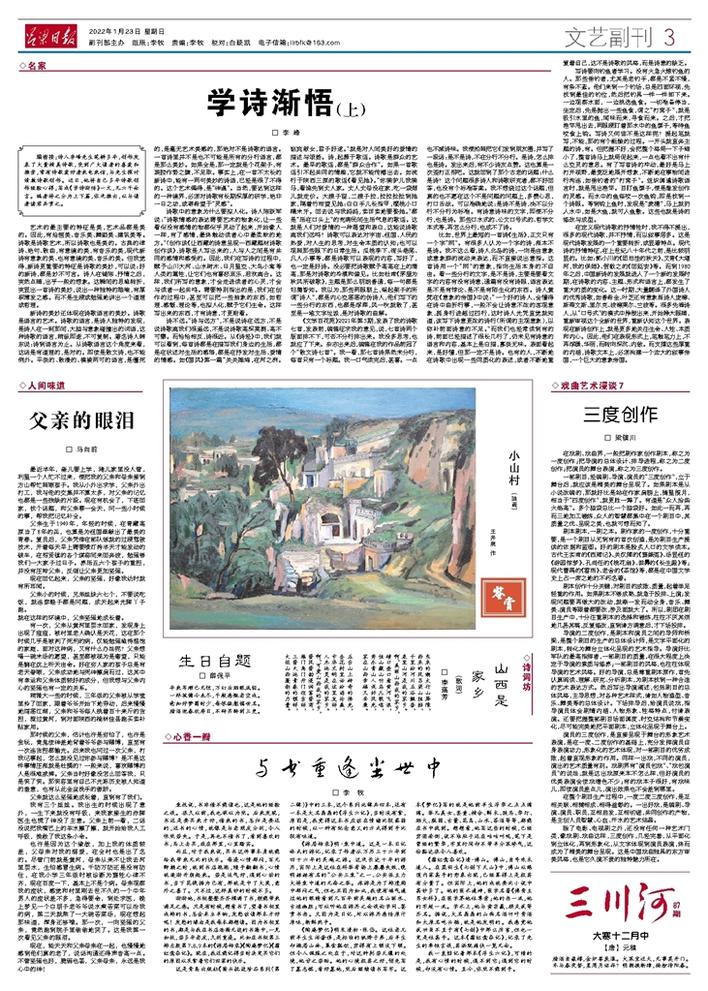编者按:诗人李峰先生笔耕多年,创作发表了大量精美诗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推崇,常有诗歌爱好者来电来信,与先生探讨请教诗歌创作。近日,他将自己多年诗歌创作经验心得,写成《学诗渐悟》一文,凡六千余言。编者将之分为上下篇,依次推出,以与读者诸君共赏之。
艺术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美,艺术品都是美的。因此,有绘画美、音乐美、舞蹈美、建筑美等。诗歌是诗歌艺术,所以诗歌也是美的。古典的律诗、绝句、散曲,有意境的美,有音乐的美,现代新诗有意象的美、也有意境的美、音乐的美。但我觉得,新诗更重要的特征是诗歌的美妙,可以说:好的新诗,都是妙不可言。诗人在铺陈、抒情之后,突然点睛,出乎一般的想象。这瞬间的思维转折,突显出一首诗的美妙,说出一种独特的隐喻,有厚积薄发之感。而不是生硬或勉强地讲出一个道理或哲理。
新诗的美妙还体现在诗歌语言的美妙。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的语言,是诗人独特的发现,是诗人在一刹那间,大脑与意象碰撞出的词语,这种诗歌的语言,稍纵即逝,不可复制。著名诗人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从诗歌语言这个角度来看,这话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即使是散文诗,也不能例外。平淡的、散漫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是僵死的,是毫无艺术美感的,那绝对不是诗歌的语言。一首诗里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的分行语言,都是那么美妙。如果全是,那一定就是个花架子,有装腔作势之嫌,不足取。事实上,在一首不太长的新诗中,能有一两句美妙的诗语,已经是很了不得的。这个艺术偶得,是“神遇”。当然,要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必须对诗歌有长期深厚的研学,绝非一日之功,或寄希望于“灵感”。
诗歌中的意象为什么要拟人化。诗人陈跃军说:“诗歌情感的表达需要艺术的物象化,让一些看似没有感情的物都似乎灵动了起来,开始像人一样,有了感情,最终触动读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创作谈《让西藏的诗意呈现—西藏题材诗歌创作谈》,诗歌是人写出来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共同的感情和感受的。因此,我们在写诗的过程中,赋予山川大河、山水树木、日月星空、大鸟小禽等人类的属性,让它们也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样,我们所写的意象,才会走进读者的心灵,才会与读者一起共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甚至可以把一些抽象的东西,如哲理、感慨、理论等,也拟人化,赋予它们生命。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诗意,才更耐看。
诗不远。“诗与远方”,不是说诗在远方,不是说诗歌离我们很遥远,不是说诗歌高深莫测、高不可攀。而恰恰相反,诗很近。从《诗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每首诗都是在描写我们身边的生活,都是在状述对生活的感悟,都是在抒发对生活、爱情的情感。如《国风》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对人间美好的爱情的描述与颂扬。诗,起源于歌谣。诗歌是群众的艺术。最早的歌谣,都是“群众合作”。如果一首歌谣引不起共同的情趣,它就不能传播出去。如流行于陕西三原的歌谣《看见她》。“你骑驴儿我骑马,看谁先到丈人家。丈人丈母没在家,吃一袋烟儿就走价。大嫂子留,二嫂子拉,拉拉扯扯到她家,隔着竹帘望见她:白白手儿长指甲,樱桃小口 糯米牙。回去说与我妈妈,卖田卖地要娶她。”都是“活在口头上”的充满民间生活气息的歌谣。这就是人们对爱情的一种渴望和表白,这能说诗歌离我们远吗?诗歌可以表达对宇宙、祖国、人民的热爱,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本质的认知;也可以观照那些眼下的日常生活。瓜桃李下、街头巷尾、凡人小事等,都是诗歌可以表现的内容,写好了,也一定是好诗。没必要把诗歌赋予高高在上的清高,那是对诗歌的冷漠和偏见。比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主题是那么明朗普通,每一句都是妇孺皆知。我以为,那些两眼朝上,端起架子的所谓“诗人”,都是内心空荡荡的伪诗人,他们写下的一些分行的东西,也都是浮萍,风一吹就散了,甚至是一堆文字垃圾,是对诗歌的曲解。
《文学百花苑》2021年第5期,发表了我的诗歌七首,发表前,编辑征求我的意见,说,七首诗两个版面排不下,可否不分行排出来。我没多思考,也就应了下来。杂志出来后,编辑在我的作品前冠了个“散文诗七首”。我一看,那七首诗果然未分行,每首只有一个标题。我一口气读完后,甚喜。一点也不减诗味。我便拍照把它们发到朋友圈,并写了一段话:是不是诗,不在分行不分行。是诗,怎么排也是诗。发出来后,有不少诗友点赞。这也算是一次歪打正招吧。这就回到了那个古老的话题:什么是诗?这个问题很多诗人和诗歌研究者,都不好回答,也没有个标准答案。我不想绕过这个话题,但真的也不愿在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多费心思,打口舌战。可以准确地说:是诗不是诗,决不以分行不分行为标准。有诗意诗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是诗。那些口水式的、公文口号式的、哲学文本式等,再怎么分行,也成不了诗。
比如,世界上最短的一首诗《生活》,正文只有一个字“网”。有很多人认为一个字的诗,根本不是诗。我不这么看,诗人北岛的诗,一向是由意象或意象群的流动来表达,而不直接说出意指。这首诗用一个“网”的意象,指向生活本身的不自由。看一些分行的文字,是不是诗,主要是要看文字的内容有没有诗意,通篇有没有诗眼,语言表达是不是有悖论、是不是有陌生化的东西。诗人黄梵在《意象的帝国》中说:“一个好的诗人,会懂得在诗中曲折行事,一般不会让诗意不浓的客观意象,孤身行进超过四行,这时诗人光凭直觉就知道,该写下诗意更浓的诗行(所谓的主观意象),以弥补前面诗意的不足。”而我们也经常读到有的诗,前面已经描述了很长几行了,仍未见有诗意的语言和内容,基本上是白描,寡淡无味。表面看起来,是好懂,但那一定不是诗。也有的人,不断地在诗歌中出现一些同质化的表述,或者不断地重复着自己,这不是诗歌的风格,而是诗意的缺乏。
写诗要向钓鱼者学习。没有火急火燎钓鱼的人。那些垂钓者,尤其是老钓手,都是不紧不慢,有条不紊。他们来到一个钓场,总是四面环视,先找到最佳的钓位,然后把钓具一件一件卸下来。一边观察水面, 一边挑选鱼食。一切准备停当,坐定后,先是抛出一些鱼食,谓之“打窝子”,就是吸引水里的鱼,闻味而来,寻食而来。之后,才把渔竿甩出去,两眼硬盯着那水中的鱼漂子,等待鱼咬食上钩。写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提起笔就写,不能,那的有个酝酿的过程。一开头就直奔主题的诗,有。但把握不好,会把整个格局一下子缩小了,整首诗马上就局促起来,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空灵的意思。有了写首诗的冲动,最好是马上打开视野,最宽泛地展开想象,不断地在事物间进行沟连,如垂钓者的“打窝子”。组织调遣诗歌语言时,就是甩出渔竿。目盯鱼漂子,便是激发创作的灵感。而水中的鱼每咬一次鱼钩,即是找到一个诗眼。等到钩上鱼时,发现是“麦穗”,马上就扔入水中,如是大鱼,就可入鱼敷。这些也就是诗的修改与成型。
在定义现代诗歌的抒情性时,我不得不提出,很多的现代诗歌,并不抒情,而以叙事居多。这是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或显著特点。现代诗的抒情特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是比较明显的。比如: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贺敬之的《回延安》等。而到1980年之后,中国新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诗歌的内容、主题、形式和语言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这一时期,大量翻译了外国诗人的优秀诗歌,如普希金、叶芝还有意象派诗人庞德、斯蒂文斯、里尔克、波德莱尔、兰波等。很多先锋诗人,从“口号式”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开始睁大眼睛,重新审视这个全新的世界,重新认知这个世界。表现在新诗创作上,就是更多地关注生命、人性、本质和内心。因此,他们在表现形式上,笔触笔力上,不再浮躁、华丽,而转向深沉、内敛。而支撑这些厚重的内涵,诗歌文本上,必须构建一个宏大的叙事帝国,一个巨大的意象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