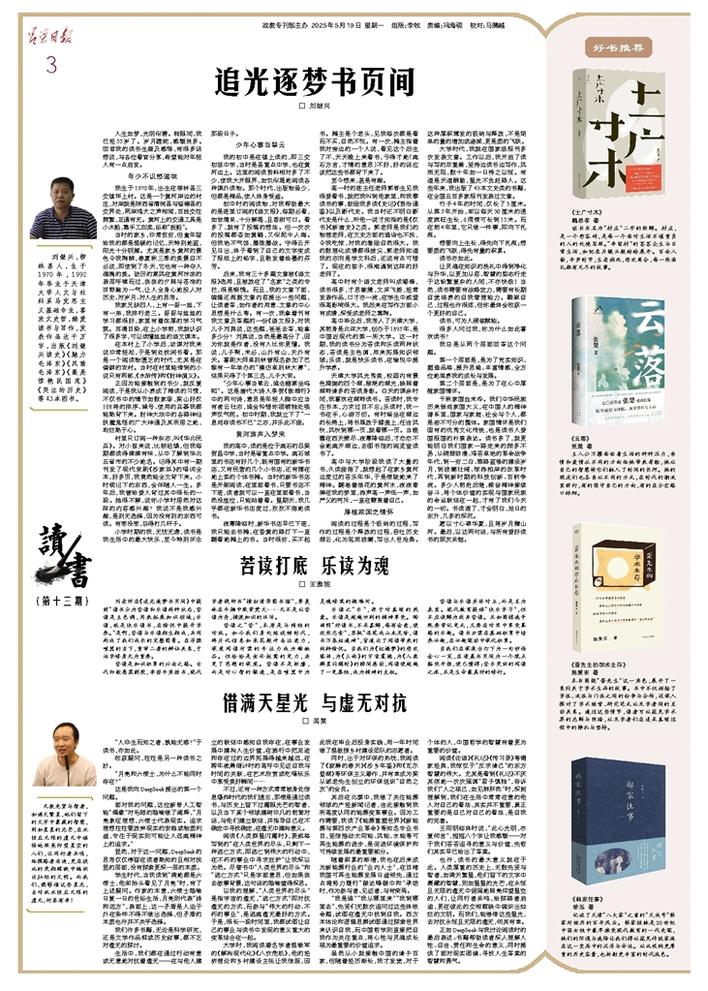人生如梦,光阴似箭。转眼间,我已经55岁了。岁月蹉跎,感慨良多。回首我的读书生涯及感悟,有很多话想说,与各位看官分享,希望能对年轻人有一点启发。
年少不识愁滋味
我生于1970年,出生在柳林县三交镇坪上村。这是一个黄河岸边的村庄,对岸就是陕西省清涧县与绥德县的交界处,两岸鸡犬之声相闻,百姓交往频繁,互通有无。黄河上的交通工具是小木船,靠手工划桨,俗称“扳船”。
当时的家乡,非常贫穷,但童年留给我的都是温暖的记忆,天特别地蓝,阳光十分明媚。尤其是家乡黄河的景色令我陶醉,春夏秋三季的美景自不必说,即使到了冬天,它也有一种夺人魂魄的美。劲厉的寒风在黄河冰冻的表层呼啸而过,淡淡的夕照与苍凉的田野融为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人生的思考。
我家兄妹四人,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弟,我排行老三。哥哥与姐姐的学习都很好,家里有着浓厚的学习气氛。耳濡目染,在上小学前,我就认识了很多字,可以读懂姐姐的语文课本。
在本村上了小学后,功课对我来说非常轻松,于是到处找闲书看。那是一个阅读物匮乏的时代,尤其是在偏僻的农村。当时在村里能借到的小说只有两部,《水浒传》和《封神演义》。
正因为能接触到的书少,就反复阅读,于是我从小养成了精读的习惯,不仅书中的情节如数家珍,梁山好汉108将的排序、绰号、使用的兵器我都能熟背下来。封神大戏中的各路神仙妖魔鬼怪的广大神通及其所居之地,均烂熟于心。
村里只订阅一种杂志,叫《华北民兵》。对小孩来说,比较枯燥,但我每期都读得津津有味,从中了解到华北五省市的不少地名。记得其中有一期刊发了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唱词全本,好多页,我竟然能全文背下来。小时候记下的东西,会伴随人一生。多年后,我曾给爱人背过其中很长的一段。她很不解,说你小学时居然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我说不是我感兴趣,是别无选择,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读。有枣没枣,总得打几杆子。
小学时期的我,无忧无虑,读书是我生活中的最大快乐,至今特别怀念那段日子。
少年心事当拏云
我的初中是在镇上读的,即三交初级中学,当时是县重点中学,也在黄河边上。这里的阅读资料相对多了不少,使我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课外读物。那个时代,出版物虽少,但都是精品,使人终身受益。
初中时的阅读物,对我帮助最大的是班里订阅的《语文报》,每期必看,如饮清泉,十分解渴,且香甜可口。看多了,就有了投稿的想法。但一次次的投稿都杳如黄鹤,又似泥牛入海。但我绝不气馁,屡败屡战。守得云开见日出,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文字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且散发着油墨的芬芳。
后来,我有三十多篇文章被《语文报》选用,且被放在了“名家”之类的专栏,很是惭愧。而且,我的文章下面,编辑还根据文章内容提出一些问题,让读者答,如作者的用意、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等。有一次,我拿着刊有我文章及答题的一份《语文报》,对我儿子刘典说,这些题,爸爸去答,能拿多少分?刘典说,当然是最高分了,因为你就是作者,没有人比你更懂。我说,儿子啊,未必,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喜剧大师卓别林曾报名参加了巴黎有一年举办的“模仿卓别林大赛”,结果只得了个第三名,儿子大笑。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这是唐代大诗人李贺《致酒行》中的两句诗,意思是年轻人胸中应当有凌云壮志,谁会怜惜你困顿独处唉声叹气呢。初中时期,我就立下了“一息尚存读书不已”之志,并乐此不疲。
黄河涛声入梦来
我的高中,读的是位于离石的吕梁贺昌中学,当时是省重点中学。离石城里的书店有好几个,既有国有的新华书店,又有民营的几个小书店,还有摆在地上卖的个体书摊。当时的新华书店是开架阅读,在里面看书,只要书店不下班,读者就可以一直在里面看书,当然没座位,只能站着看。星期天,我几乎都在新华书店度过,孜孜不倦地读书。
夜幕降临时,新华书店早已下班,我只能去书摊,在昏黄的路灯下一直翻看地摊上的书。当时很穷,买不起书。摊主是个老头,见我每次都是看而不买,自然不悦。有一次,摊主指着我对旁边的一个人说,看见这个后生了不,天天晚上来看书,亏得才地(离石方言,才情的意思)不好,好的话应该把这些书都背下来了。
至今想来,甚是有趣。
高一时的班主任老师郭晋生见我很爱看书,就把我叫到他家里,和我聊读书的事,鼓励我多读《史记》《资治通鉴》以及断代史。我当时还不明白断代史是什么,听他一说才知指的是《汉书》《新唐史》之类。郭老师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在文史方面的造诣也不浅,令我吃惊,对我的激励自然很大。我的数理化成绩都很拔尖,郭老师知道我的志向是学文科后,还说有点可惜了。现在的孩子,很难遇到这样的好老师了。
高中时有个语文老师叫成锡锋,读书很多,才思敏捷,文采飞扬,经常发表作品,口才亦一流,在学生中威望很高影响很大。我后来在写作方面小有成绩,深受成老师之熏陶。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了天津大学,其前身是北洋大学,创办于1895年,是中国近现代的第一所大学。这一时期,我的读书分为苦读和乐读两种状态,苦读是主色调,用来拓展知识领域;乐读,就是快乐读书,在愉悦中提升学养。
天津大学风光秀美,校园内有景色旖旎的四个湖,潋滟的湖光,映照着湖畔诸多的苦读身影。白天的课余时间,我喜欢在湖畔读书。苦读时,我专注书本,力求过目不忘;乐读时,我一书在手,心游万仞。有时端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将书展放于膝盖上,任由风吹,风吹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当晚霞在西天燃尽、夜幕降临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湖边,去图书馆的阅览室读书了。
高中与大学阶段我读了大量的书,久读疲倦了,就想起了在家乡黄河边度过的苦乐年华,于是便陡地来了精神。翻卷着浪花的黄河水,夜夜澎湃在我的梦里,涛声高一声低一声,如严父的呵斥,一直在鞭策着自己。
厚植家国之情怀
阅读的过程是个吸纳的过程,写作的过程是个释放的过程,吞吐历史烟云,化为笔底波澜,写出人世沧桑。这种厚积薄发的吸纳与释放,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或递减,更是质的飞跃。
大学时代,我就在国家级报刊多次发表文章。工作以后,我开启了读与写的双重奏,坚持边读书边写作,风雨无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有道是天道酬勤,星光不负赶路人。这些年来,我出版了43本文史类的书籍,在全国五百多家报刊发表过文章。
竹子4年的时间,仅长了3厘米。从第5年开始,却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生长,6周便可长到15米。而在前4年里,它只做一件事,即向下扎根。
想要向上生长,得先向下扎根;想要质的飞跃,得先有量的积累。
读书亦如此。
让灵魂在知识的洗礼中得到净化与升华,以更加从容、智慧的姿态行走于这纷繁复杂的人间,不亦快哉!当然,读书需要有战略定力,需要有长期自觉培养的自我管理能力。雕琢自己,过程也许很疼,但你最终会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读书,可为人硬核赋能。
很多人问过我,你为什么如此喜欢读书?
我总是从两个层面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是为了充实知识、塑造品格,提升思维、丰富情感,全方位地滋养我的成长与发展。
第二个层面是,是为了在心中厚植家国情怀。
千秋家国血未冷。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家国大义,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家国情怀是我们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读书人爱国报国的朴素表达。读书多了,就更能明白我们国家一路走来的颇多不易,从硝烟弥漫、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到一穷二白、筚路蓝缕的建设岁月,到波澜壮阔、惊涛拍岸的改革时代,再到新时期的科技创新、百舸争流。多少人前赴后继,振奋精神接续奋斗,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一切。书读透了,才会明白,旭日的东升,几多的深沉。
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最后,以这两句话,与所有爱好读书的朋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