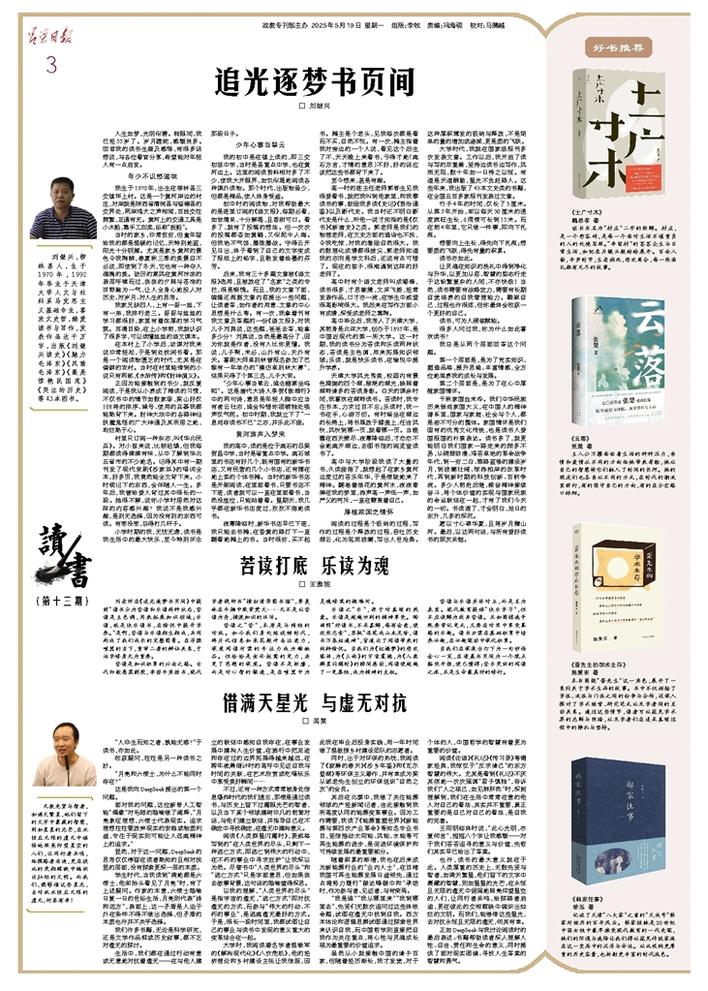“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于读书,亦如此。
收获疑问,往往是另一种读书之妙。
“月亮和六便士,为什么不能同时存在?”
这是我向DeepSeek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面对我的问题,这位新晋人工智能“偶像”对毛姆的隐喻做了阐释,“月亮象征理想,六便士代表现实。追求理想往往要放弃现实的安稳或物质利益,专注于现实则可能让人远离精神上的追求。”
显然,对于这一问题,DeepSeek的思考仅仅停留在读者熟知的且相对浅显的层面,没有探索更深一层的本质。
学生时代,当我读到“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时,有了上述疑问。作家的本意,六便士隐喻日复一日的世俗生活,月亮则代表“诗和远方”,表面上,这一矛盾是人迫于外在条件不得不做出选择,但矛盾的本质也许并不关乎选择。
我们许多书籍,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文学作品抑或历史叙事,都不乏对虚无的探讨。
生活中,我们都在通过行动有意或无意地对抗着虚无——在与他人建立的联结中感知自我存在,在事业发展中建构人生价值,在旅行中把足迹和存在过的边界拓展得越来越远,在跨年凌晨倒计时的高呼中见证自我与时间的关联,在艺术欣赏或吃喝玩乐中享受美好瞬间……
不过,还有一种方式常常被身处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遗忘,那便是通过读书,与历史上留下过耀眼光芒的智者,以及当下某个领域建树非凡的前辈对话,与他们建立联结,并指导自己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虚无中建构意义。
阅读《人类群星闪耀时》,茨威格写到的“在人类世界的尽头,只剩下一种逃亡方式,即逃亡到伟大的行动中,在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让我深以为然。尽管书中“人类世界的尽头”和“逃亡方式”只是字面意思,但如果淡去故事背景,这句话的隐喻值得深思。
以我的理解,“人类世界的尽头”是指宇宙的虚无,“逃亡方式”即对抗虚无的方式,而参与“伟大的行动、不朽的事业”,是逃离虚无最好的方式。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试图让自己的事业与读书中发现的意义重大的变革结合在一起。
大学时,我阅读著名学者温铁军的《解构现代化》《八次危机》,他的经济理论和乡村建设主张让我信服,因此我在毕业后投身实践,用一年时间做了温教授乡村建设团队的志愿者。
同时,出于对环保的热忱,我阅读了《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和《瓦尔登湖》等环保主义著作,并有幸成为梁从诫老先生创立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员。
其后在北漂中,我做了关注能源领域的产经新闻记者,由此接触到我所高度认同的能源变革事业。因为工作需要,我读了《能源重塑世界》《新能源与第四次产业革命》等知名专业书目,坚信推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进步,是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部分。
随着积累的渐增,我也在后来成为新能源行业的“业内人士”,在目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日益领先,通过点滴努力履行“碳达峰碳中和”承诺时,作为参与者、见证者,与有荣焉。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先贤们无数次追问过这些终极命题,试图在虚无中找到自我。西方本体论和逻辑思辨试图通过探索世界来认识自我,而中国哲学则直接把自我作为关注重点,将心性与灵魂成长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虽然从小就接触中国的诸子百家,但随着经历渐长,我才发觉,对于个体的人,中国哲学的智慧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
阅读《论语》《礼记》《传习录》等儒家经典,我惊叹于“反求诸己”的东方智慧的伟大。尤其是看到《礼记》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强调“君子慎独”,告诉我们“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时,深刻理解到,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在意的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是自我的完善。
王阳明临终时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短短八个字让我感慨——对于我们苦苦追寻的意义与价值,先哲们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
也许,读书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人类厚重的历史上,无数先贤与智者,如满天繁星,他们留下的文字中裹藏的智慧,则如星星的光芒,在永恒且无限的虚无中倔强地照亮仰望星空的人们,让同行者共鸣,给探路者启迪,更在彼此的交相辉映中编织出灿烂的文明。而我们,能够借这些星光,去对抗永恒且无限的虚无,何其有幸。
正如DeepSeek与我讨论阅读时的最后表述:书籍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人性、自由、责任和生命的意义,同时提供了面对现实困境、寻找人生答案的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