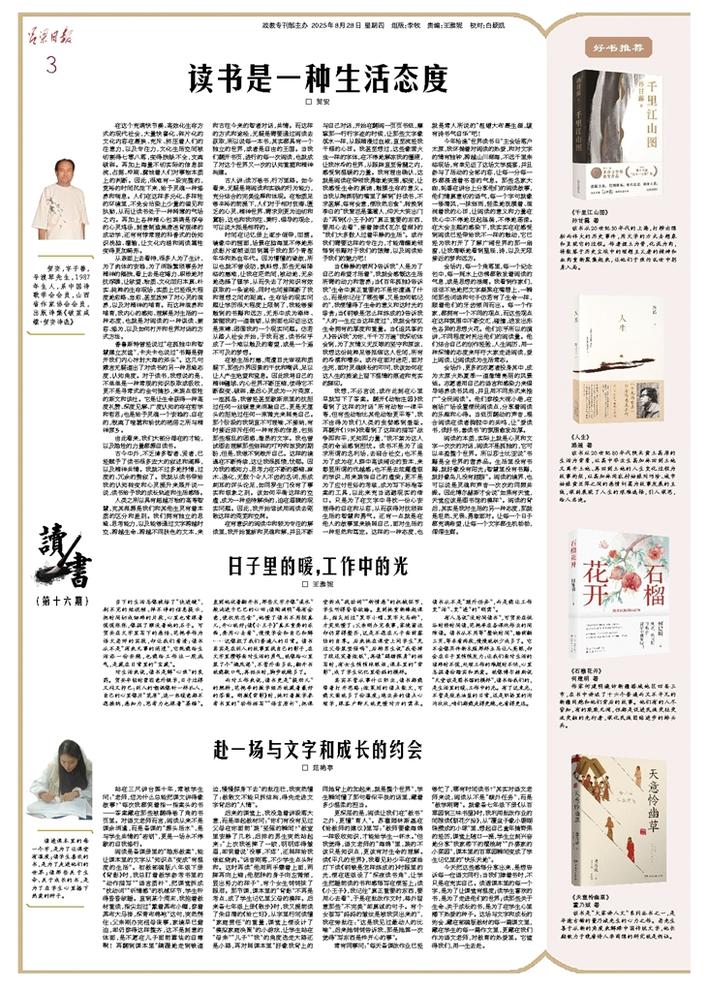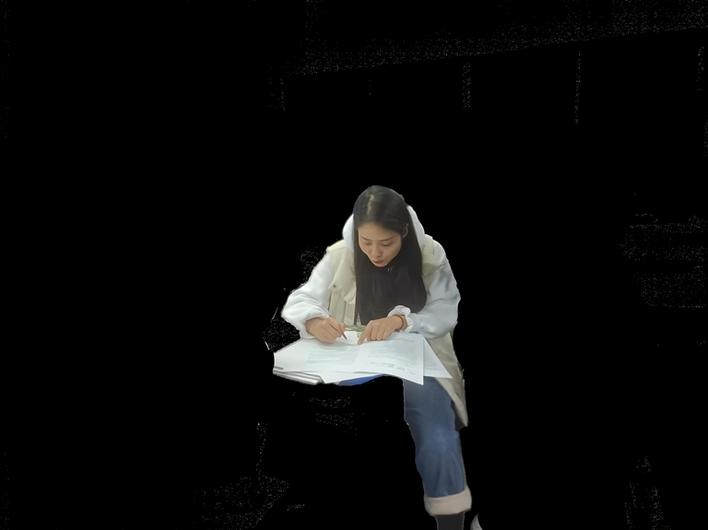站在三尺讲台第十年,常被学生问:“老师,您为什么总能把课文讲得像故事?”每次我都笑着指一指案头的书——答案藏在那些被翻得卷了角的书页里。对语文老师而言,阅读从来不是课余消遣,而是备课的“源头活水”,是与学生共情的“密钥”,更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自我修行。
阅读是备课册里的“隐形教案”,能让课本里的文字从“知识点”变成“有温度的生活”。初教部编版八年级下册《背影》时,我总盯着教学参考书里的“动作描写”“语言质朴”,把课堂拆成“找动词”“析情感”的机械环节,学生听得昏昏欲睡。直到某个周末,我抱着教材重读,指尖划过“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这句,突然愣住:父亲刚办完祖母丧事,家境早已窘迫,却仍穿得这样整齐,这不是刻意的体面,是不愿在儿子面前露怯的自尊啊!再翻到课本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的批注栏,我突然懂了:教散文不能只拆结构,得先走进文字背后的“人情”。
后来的课堂上,我没急着讲段落大意,而是举起教材问:“你们有没有见过父母在你面前‘装’坚强的瞬间?”教室里安静了几秒,后排的男生突然站起来:“上次我爸摔了一跤,明明疼得皱眉,却笑着说‘没事,不疼’,还照样给我做红烧肉。”话音刚落,不少学生点头附和。这时再读“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有个女生悄悄抹了眼泪。那节课,课本里的“背影”不再是考点,成了学生记忆里父母的模样。后来备七年级上册《散步》时,我又提前读了朱自清的《给亡妇》,从字里行间读懂“家庭责任”的重量,课堂上便设计了“模拟家庭决策”的小游戏,让学生站在“母亲”“儿子”“我”的角度选走大路还是小路,再对照课本里“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学生瞬间懂了那句看似平淡的话里,藏着多少温柔的担当。
更深层的是,阅读让我们在“教书”之外,更懂“育人”。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里写:“教师要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才能给学生一杯水。”但我觉得,语文老师的“海绵”里,装的不该只是知识点,更该有对生命的理解。读《平凡的世界》,我看见孙少平在煤油灯下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眼里的光,便在班级设了“深夜读书角”,让学生把睡前读的书和感悟写在便签上;读《小王子》,我记住“真正重要的东西,要用心去看”,于是在批改作文时,格外留意那些“不完美”却真诚的句子。有个女孩写“妈妈的皱纹是被我哭出来的”,我在旁批注:“这是我见过最动人的比喻”,后来她悄悄告诉我,那是她第一次觉得“写东西是件开心的事”。
常有同事问:“每天备课改作业已经够忙了,哪有时间读书?”其实对语文老师来说,阅读从不是“额外任务”,而是“教学刚需”。就像备七年级下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我利用批改作业的间隙读《朝花夕拾》,从“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里,想起自己童年摘野果的经历,课堂上随口一提,学生立刻兴奋地分享“我家楼下的樱桃树”“外婆家的小菜园”,课本里的百草园瞬间变成了学生记忆里的“快乐天地”。
今天把这些感悟分享出来,是想告诉每一位语文同行:当我们捧着书时,不只是在充实自己。读透课本里的每一个字,是为了让课堂有温度;读学生喜欢的书,是为了走进他们的世界;读那些关于生命、关于成长的书,是为了在学生心里播下热爱的种子。这场与文字和成长的约会,藏在部编版教材的每一篇课文里,藏在学生的每一篇作文里,更藏在我们作为语文老师,对教育的热爱里。它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