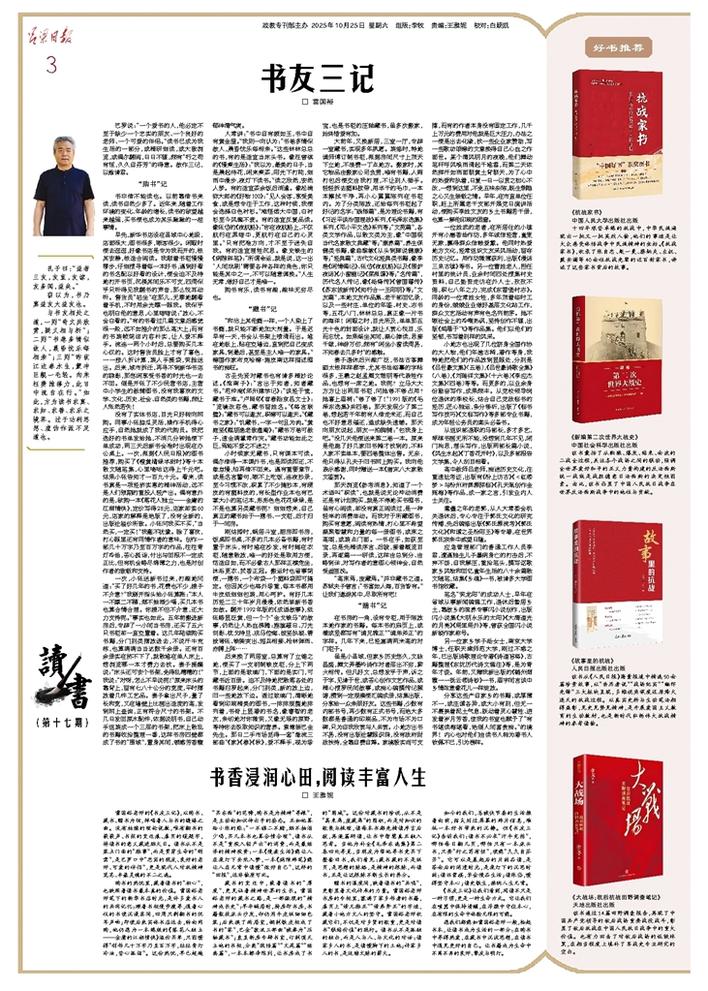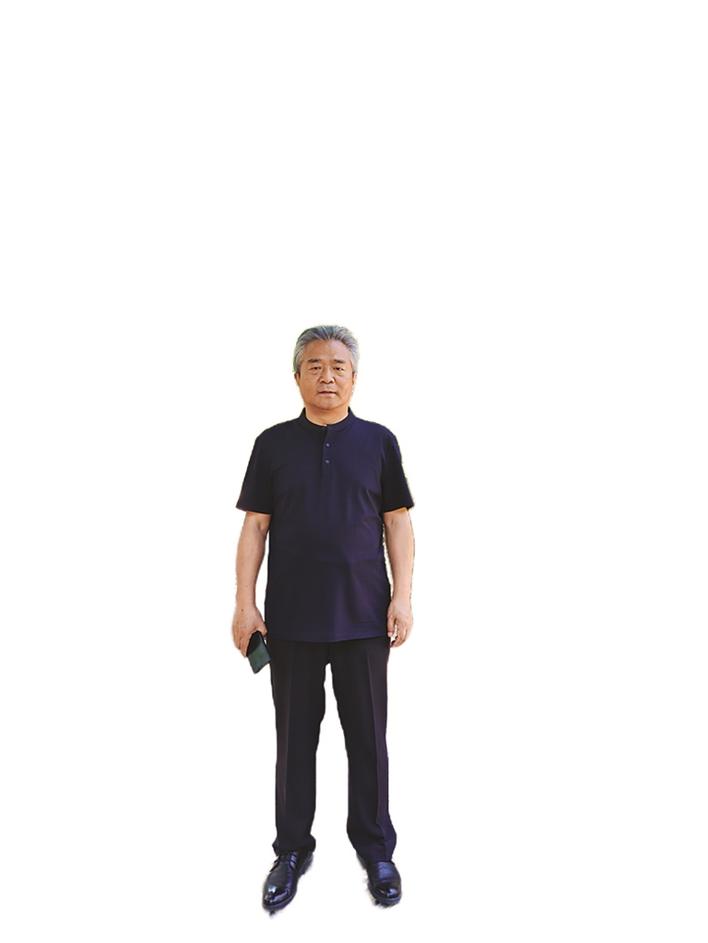巴罗说:“一个爱书的人,他必定不至于缺少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良好的老师、一个可爱的伴侣。”读书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或精研细读,或大致浏览,或偶尔翻阅,日日不辍,颇有“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的得意。故作三记,以飨诸君。
“购书”记
书非借不能读也。以前靠借书来读,读书自然少多了。近年来,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年龄的增长,读书的欲望越来越强,买书便也成为其乐融融的一桩事情。
早先,新华书店设在县城中心地段,店面很大,图书很多,顾客很少。闲暇时便去逛逛,好像书店是专为我而开的,极其安静,极适合阅读。我顺着书柜慢慢移步,仔细搜寻着每一本好书,遇到好看的书名配以好看的设计,便会迫不及待地打开书页,沉浸其间乐不可支,四周似乎只听得见我翻书的声音,那么悦耳动听。售货员“枯坐”在那儿,无聊地翻看着手机,不时用余光瞟一眼我。我似乎也明白他的意思,心里暗暗说:“放心,不会白看的。”有的书看过几篇文章后感觉很一般,远不如推介的那么高大上;而有的书装帧简洁内容朴实,让人爱不释手。流连一两个小时后,总要购买几本心仪的。这时售货员脸上才有了喜色,一一按八折计算,装入手提袋,笑脸送出。后来,城市拆迁,再寻不到新华书店的踪影,那悠闲享受书香的时光也一去不回。倒是开张了不少民营书店,主营中小学生的教辅图书,没有我喜欢的文学、文化、历史、社会、自然类的书籍,颇让人怅然若失!
没有了实体书店,目光只好转向网购。同事小张脑瓜灵活,操作手机得心应手,自然她就成了我的代购员。我把选好的书单发给她,不消几分钟她便下单成功,两三天后新书会准时出现在办公桌上。一次,根据《人民日报》的图书推荐,购买了《橙黄橘绿半甜时》等十本散文随笔集,心里嘀咕这得上千元吧。结果小张告知才一百九十元。看来,读书真是一项经济实惠的精神活动,远不是人们预期的重投入轻产出。偶有意外的是,欲购一本《落花人独立——金庸的江湖情侠》,定价写得28元,店家却卖60元,店家的解释是绝版了,没有全新的,出版社溢价所致。小张问我买不买,“当然买,一定买!”我毫不犹豫。除了喜欢,打心眼里还有同情作者的意味。创作一部几十万字乃至百万字的作品,往往青灯冷油,苦心孤诣,付出与回报不一定成正比,但有机会略尽绵薄之力,也是对创作者的致敬和支持。
一次,小张送新书过来,打趣地问道:“买了好几年的书,花费也不少,嫂子不介意?”我掰开指头给小张算账:“本人一不嫖二不赌,烟不抽酒少喝,买几本书也算合情合理。你嫂不但不介意,还大力支持呢。”事实也如此。五年前搬进新房后,专辟了一小间当书房,还买了五六只书柜却一直空置着。这几年陆续购买书籍,分门别类摆放进去,不说汗牛充栋,也算满满当当达数千余册。还有百余册实在挤不下了,就散堆在单人床上,想浏览哪一本才费力去找。妻子提醒说:“床头还可安个书架,免得乱糟糟的!”我说:“对呀,怎么不早说呢!”原来床头的靠背上,留有七八十公分的宽度,平时摆放着几件工艺品。妻子拿出尺子,量了长和宽,又在墙壁上比画出适度的高,发到网上查询,正有符合尺寸的书架。不几日发回原木配件,依据说明书,自己动手组装成一个三层的书架,把床上散乱的书籍收拾整理一番,这样书房四壁都成了书的“围城”,置身其间,顿感芳香馥郁神清气爽。
人常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则一向认为:“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这些林林总总的书,有的是适宜当床头书。像汪曾祺的《慢煮生活》:“我以为,最美的日子,当是晨起侍花,闲来煮茶,阳光下打盹,细雨中漫步,夜灯下读书。”读之欣然,安然入梦。有的适宜茶余饭后消遣。像松浦弥大郎的《好物100》:“见人会客,享受美食,或是想专注于工作,这种时候,我便会选择白色衬衫。”难怪偌大中国,白衬衫至今风靡不衰。有的适宜反复品读。像张岱的《夜航船》:“你在夜航船上,不仅航行在黑暗中,更航行在自己的心灵里。”只有把准方向,才不至于迷失自我。有的适宜理性沉思。像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人生无常,做好自己才是唯一。
购书有乐,读书有趣,趣味无穷尽也。
“藏书”记
“和沾上其他瘾一样,一个人染上了书瘾,就只能不断地加大剂量。于是迟早有一天,书会从书架上喷涌而出。堆在地板上,贴在空墙边,直到把自己变成家具,到最后,甚至是主人唯一的家具。”德国作家布克哈德·施皮南这样描述囤书的痴狂。
古圣先贤对藏书也有诸多精妙论述。《淮南子》:“言出于知者,知者藏书。”范仲淹《邠州建学记》:“谈经于堂,藏书于库。”卢照邻《首春贻京邑文士》:“览镜改容色,藏书留姓名。”《格言联璧》:“藏书可以邀友,积德可以邀天。”《藏书之家》:“饥藏书,一字一句且为肉。”黄庭坚《题胡逸老致虚庵》:“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籯常作灾。”藏书功能如此之巨,焉能不爱之不迷之?
小时候家无藏书,只有课本可读。偶尔借得一本课外书,也是即读即还,不敢怠慢,怕再借不回来。遇有重要章节,或是名言警句,顾不上吃饭,连夜抄录,至今习惯不改,积累了不少摘抄本,有硬皮的有塑料皮的,有长型作业本也有巴掌大小的笔记本,形形色色花花绿绿,是不是也算另类藏书呢?细细想来,自己真正的藏书始于一撂书、一支柜,后才归于一间房。
刚结婚时,蜗居斗室,厨房即书房,饭桌即书桌,不多的几本必备书籍,有时置于床头,有时堆在沙发,有时搁在衣柜,随意散放,唯一的好处是取用方便,恬适自如,而不必像古人那样正襟危坐,沐浴更衣、焚香正冠。搬运时也省事简便,一撂书,一个布袋一个塑料袋即可搞定。但因其少也格外珍重,每本书都用牛皮纸细细包装,用心呵护。有好几本历经二三十年岁月漫漫,依然崭新书香如故。翻开1992年版的《成语故事》,纸张略显泛黄,但一个个“金戈铁马”的故事,仍然让人热血沸腾:旌旗蔽日、刀光剑影、枕戈待旦、戎马倥偬、披坚执锐、箭拔弩张、铁骑突出、短兵相接、枪林弹雨、赤膊上阵……
后来换了两居室,总算有了立锥之地,便买了一支钢制铁皮柜,分上下两节,上面的是玻璃门,下面的是实门,可藏书近百册。迫不及待地把散落各处的书籍归罗起来,分门别类,新的放上边,旧一些地放下边。透过玻璃门,清晰地看到印刷精美的图书,一排排规整地排列着,书脊上显著的书名,像睿智的老友,亲切地对你微笑,又像无垠的原野,等待你去汲取知识的营养。素尊崇巴金先生。那日二手市场觅得一套“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不释手,视为珍宝,也是书柜的压轴藏书,虽多次搬家,始终惜爱有加。
大前年,又换新居,三室一厅,专辟一室藏书,实现多年夙愿。装修时,特地请师傅订制书柜,根据房间尺寸上顶天下立地,不浪费一丁点地方。搬家时,其它物品由搬家公司负责,唯有书籍,入箱打包后便交由我打理,不让别人插手。轻轻拆去塑料胶带,用半干的毛巾,一本本擦拭干净,再小心翼翼陈列在书柜内。为了分类陈放,还给每列书柜起了好记的名字:“践悟篇”,是为理论书籍,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毛泽东选集》系列,《邓小平文选》系列等;“文苑篇”,各类文学作品,以散文类为主,像“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等;“康养篇”,养生保健类书籍,像曲黎敏《从头到脚说健康》等;“经典篇”,古代文化经典类书籍,像李渔《闲情偶记》、张岱《夜航船》以及《围炉夜话》《小窗幽记》《菜根谭》等;“名传篇”,历代名人传记,像《杨绛传》《曾国藩传》《苏东坡新传》《知行合一王阳明》等;“文友篇”,本地文友作品集、老干部回忆录,以及一些村庄、单位的年鉴、村史、志书等,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真正像一片书的海洋!闲暇之时,目光所及,单单那五光十色的封面设计,就让人赏心悦目,乐而忘忧。如果端坐其间,凝心捧读,思接千载,神游万仞,颇有“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的感触。
妻子退休后兴趣广泛,书法古筝舞蹈太极样样都学,尤其书法临摹的字帖很多,王羲之赵孟頫文徵明等代表性作品,也想有一席之地。我呢?立马大大方方让出两层书柜,问她够不够占用?她喜上眉梢:“够了够了!”1991版的《毛泽东选集》共四卷。那天发现少了第二卷,想起若干年前有人借走未还,而自己也不好意思催还,造成缺失遗憾。那天向朋友说起,朋友一拍胸脯:“包我身上吧。”没几天他便送来第二卷一本。原来是他跑了好几家旧书摊才找到的,不料人家不卖单本,要四卷整体出售。无奈,他只得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我向他表示感谢,同时赠送一本《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
那天浏览《参考消息》,知道了一个术语叫“积读”,也就是说无论冲动消费还是有计划购买,就是不停地买书囤书,虽有心阅读,却没有真正阅读过,是一种轻率的消费举动。而我对于所藏图书,购买有意愿,阅读有热情,打心里不希望凝聚智慧和力量的每一册图书,或束之高阁,或装点门面。一书在手,如获至宝,总是先精读序言、后跋,接着概览目录,再逐篇一一研读,这样由总到分、由略到详,对写作者的意图心领神会,自然受益匪浅。
“高束焉,庋藏焉。”并非藏书之道。苏轼夫子曾言:“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让我们遨游其中,尽取所有吧!
“赠书”记
在书房的一角,设有专柜,用于陈放本地作家的书籍。每本书的扉页上,或横或竖都写有“请兄雅正”“请弟斧正”的字样。几年下来,已经塞满两米高的对门柜子。
虽是小县城,但家乡历史悠久,文脉昌盛,舞文弄墨吟诗作对者层出不穷,薪火相传。但凡好文,总想发乎于声,诉之于字,见诸于世,或苦心创作文艺作品,或精心搜罗民间故事,或痴心编撰传记簇谱,攒到一定规模便汇编成册,结集出版,分享给一众亲朋好友。这些书籍,少数有内部书号,再少数有正式书号,而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印刷品,不为市场不为口碑,只为自我欣赏与人共赏。小地方出书不易,没有出版社慧眼识珠,没有政府财政扶持,全靠自费自筹。家境殷实尚可支撑,而有的作者本身没有固定工作,几千上万元的费用对他就是巨大压力,办法之一便是出去化缘,找一些企业家赞助,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换得自己心血之作面世。某个清风明月的夜晚,他们舞动笔杆呼风唤雨涌起千堆雪,而第二天依然挥汗如雨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了心中的热爱和执着,日复一日一以贯之初心不改,一想到这里,不免五味杂陈,既生恻隐之心又生崇敬之情。早年,在市直单位任职,赶上所属老干支部开展党日演讲活动,便购买李姓文友的乡土书籍若干册,也算一解他印刷的困窘。
一位姓武的老者,在所居住的小镇开有小磨香油作坊,多年诚信经营,童叟无欺,赢得群众信赖爱戴。他同时热爱地方文化,经常组织文友采风活动,留存历史记忆。用作坊微薄获利,出版《漫话三泉古镇》等书。另一位曹姓老人,担任村里的统计员,业余时间四处搜集村史资料,自己垫资走访在外人士,孜孜不倦,积七八年之力,完成《东雷堡村志》。同龄的一位常姓女性,多年顶着临时工的身份,兢兢业业做好基层文化站工作,群众文艺活动有声有色名列前茅。她不顾社会上的冷嘲热讽,坚持创作不辍,出版《鸿雁于飞》等作品集。他们以他们的坚韧,书写着别样的风采。
小地方也出现了几位跻身全国作协的大人物,他们年逾古稀,著作等身,我特地把他们的作品放到显眼处,分别是《吕世豪文集》(五卷),《吕世豪诗歌全集》(八卷),《刘瑞祥文集》(十六卷)《李应杰文集》(四卷)等等。而更多的,以业余身份勤奋写作,成果颇丰。从党校领导岗位退休的李校长,结合自己党政秘书的经历,匠心独运,条分缕析,出版了《秘书写作技巧》《文秘写作》等多部专业书籍,成为年轻公务员的案头必备书。
从组织部退职的马部长,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没想到几年不见,闭门构思,埋头写作,出版两部长篇小说,《风生水起》《丁香花开时》,以及多部报告文学集,令人刮目相看。
高中教师吕老师,痴迷历史文化,注重遗址考证,出版有《汾上访古》《<红楼梦>与汾州府渊源探秘》《孔天胤创作金瓶梅》等作品,成一家之言,引发业内人士关注。
耄耋之年的老郭,从人大常委会机关退休后,专心专注于郭氏文化的研究传播,先后编修出版《郭氏源流考》《郭氏文化》《和谐之圣汾阳王》等专著,在世界郭氏宗亲中威望日隆。
应急管理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李君,遭遇独生儿子暴病身亡的打击后,不弃不馁,自我解压,重拾笔头,撰写讴歌家乡风物和回忆童年生活的八十余篇散文随笔,结集《乡魂》一书,被诸多大学图书馆收藏。
笔名“笑龙阳”的成功人士,早年在省城从事新闻编辑工作,退休后蛰居乡土,靠故乡的滋养专事闪小说创作,出版闪小说集《大明永乐的太阳》《大清道光的月亮》《局里局外》等,曾获全国闪小说新锐作家称号。
另一位家乡学子杨女士,南京大学博士,任职天津师范大学,刚过不惑之年,已出版诗歌理论专著《诗道旨格》,古籍整理《东坑历代诗文辑注》等,是为青年才俊。年前,又赠我新出版的《鹤州烟霞一一抚云楼诗钞》一书,眉宇间言谈中乡情浓意像花儿一样绽放。
分享这些产自家乡的书籍,或厚薄不一,或庄谐各异,或大小有别,但无一不裹挟着泥土气息、跃动着灵心慧性、迸发着岁月芳香,使我的书室也赋予了“有书堪读梅堪看,绝倒人间富贵痴。”的境界!内心也对他们由读书人转为著书人钦佩不已,引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