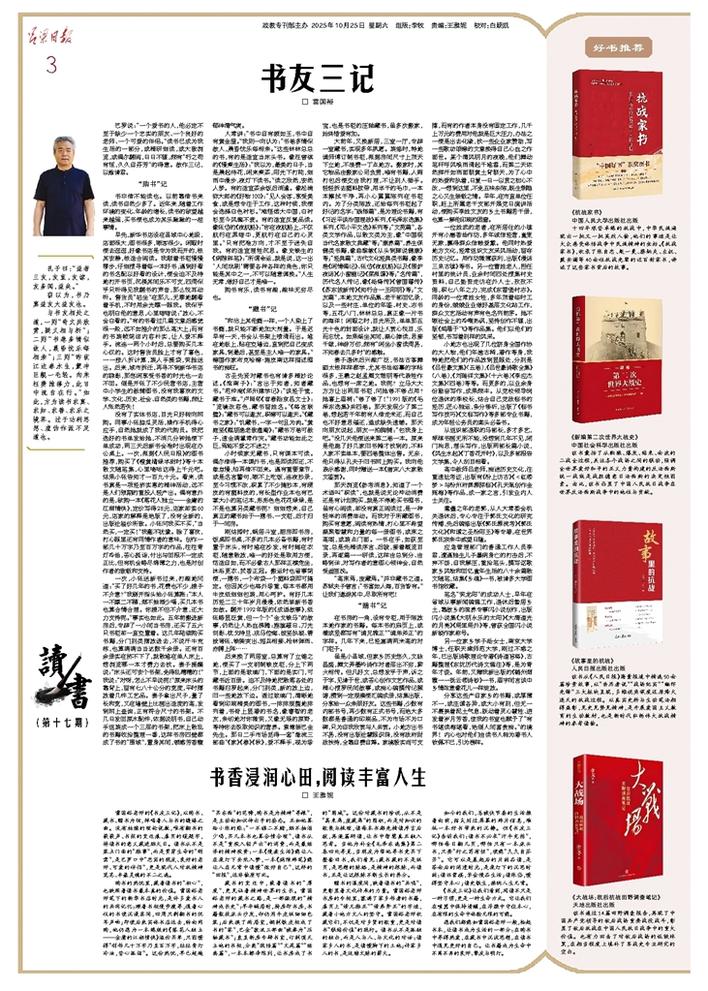雷国裕老师的《书友三记》,以购书、藏书、赠书为弦,弹唱着人与书的缱绻之曲。没有枯燥的理论说教,唯有翻书的簌簌声、书架的变迁痕、扉页的暖题字,将读书的意义藏进烟火日。读书从不是装点门面的“雅事”,而是贯穿生命的“刚需”,是巴罗口中“忠实的朋友、良好的老师、可爱的伴侣”,更是现代人对抗精神荒芜、丰盈灵魂的不二之选。
购书的热忱里,藏着读书的“初心”,也映照着读书最本真的价值。雷国裕老师笔下的新华书店时光,是许多爱书人的共同记忆:顺着书柜慢步搜寻,遇着心仪的书便沉浸其间,四周只剩翻书的悦耳声响;即便后来实体书店远去,转向网购,他仍愿为一本绝版的《落花人独立——金庸的江湖情侠》溢价买单,只因懂得“创作几十万字乃至百万字,往往青灯冷油,苦心孤诣”。这份热忱,早已超越“买东西”的范畴,购书是为精神“寻粮”,是主动向知识伸出手的姿态。正如他算给小张的账:“一不嫖二不赌,烟不抽酒少喝,买几本书也算合情合理”,读书从不是“重投入轻产出”的消费,而是最经济的精神投资:一本《慢煮生活》能让人在夜灯下安然入梦,一本《病隙碎笔》能让人在无常中读懂“做好自己”,这样的“回报”,远非物质可比。
藏书的变迁中,载着读书的“厚度”,更见证着精神世界的生长。雷国裕老师的藏书之路,是一部微观的“精神成长史”:早年蜗居时,厨房即书房,书籍散放床头沙发,却仍用牛皮纸细细包装;后来换了两居室,钢制铁皮柜成了书的“家”,巴金“激流三部曲”被奉为“压轴藏书”;直至新房专辟书室,订制顶天立地的书柜,分类“践悟篇”“文苑篇”“经典篇”,一本本擦净陈列,让书房成了书的“围城”。这份对藏书的珍视,从不是“高束焉,庋藏焉”的囤积,而是对知识的敬畏与梳理,读每本书都先精读序言后跋,再逐篇研读,让书中智慧真正融入思考。当他为补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四处寻觅,当朋友为帮他寻书竟买下整套旧书,我们看见:藏书藏的不是纸页,是思想的脉络,是精神的根脉,而读书,正是让这根脉不断生长的养分。
赠书的温度间,映着读书的“共鸣”,更彰显着文化传承的力量。雷国裕老师书房的专柜里,塞满了家乡作者的书籍,扉页上“请兄雅正”“请弟斧正”的字迹,藏着小地方文人的坚守。雷国裕老师收藏它们,不仅是对乡贤的敬重,更是对读书“联结价值”的践行。读书从不是孤独的独白,而是人与人、与文化的对话:读家乡人的书,是读懂脚下的土地;传家乡人的书,是延续文脉的薪火。
如今的我们,总被快节奏的生活推着向前,指尖划过屏幕的碎片信息,难抵一本好书带来的沉静。但《书友三记》告诉我们:读书不必求“汗牛充栋”,哪怕每日翻几页,哪怕只有一本床头书,只要“行之苟有恒”,便能“久久自芬芳”。它可以是晨起后的片刻品读,是茶余后的消遣时光,是夜灯下的沉思时刻:读汪曾祺,学会慢品生活;读张岱,懂得坚守本心;读史铁生,接纳人生无常。
《书友三记》让我们看到,阅读不只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生命方式。它让我们在喧嚣中保持清醒,在浮躁中守住本心,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无限的可能。
愿我们都能如雷国裕老师一般,拾起书本,让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购书中寻得热爱,在藏书中沉淀思想,在读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让书籍成为生命中不离不弃的良师、挚友与明灯。